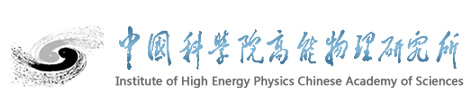回眸我国高海拔宇宙线研究
谭有恒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100049)
一、前言
自Hess的热气球实验于1912年发现宇宙辐射以来,人们一直把它当作“粒子炮弹”和宇宙物质样品,用作打开基本粒子世界大门和了解宇宙及空间环境的有力工具。但时逾百年,除了低能的太阳粒子外,人们从不知晓他们的原产地(宇宙线源)究竟在哪,因为这些以质子为主的高能原子核的行进路线早被途中的星系际和星际磁场搅拌得各向同性了。理论上,它们应与恒星进化晚期产物(如超新星爆发及其遗迹,大质量黑洞等)相联系,然而一直找不到实验的证据。新近,我国在四川稻城一海拔4400米山头新建的1平方千米级大型EAS阵列,测出蟹状星云的γ能谱已延续到PeV(1015eV),且多个河内γ源都有强劲的高于0.1 PeV的γ射线发射,即都为UHE-γ源。这证实了羊八井AS-γ阵列去年测到的来自Crab的0.45 PeVγ射线的事实,更成了这些天体是“宇宙超高能质子加速器”的指认。因为在如此高能,SSC(自同步逆康普顿散射)之类的电子源模型均已失效,只有超高能核作用产物π0的对产生能解释如此高能的γ射线的成因。这预示着历代宇宙线学者苦苦追寻的宇宙射线源(天体)的神秘面纱就要被揭开,宇宙线起源研究就能针对这些具体天体的具体极端物理条件深入展开,“UHEγ天文”的时代就要真正开启。
这使我想起1986年初,在高能所宇宙线室的一次规划会上,在介绍《西藏计划》的透明片最后,我写了“十年奋斗打基础,十年奋斗领风骚”14个大字,赢得了一片善意的笑声。都以为那不过是书生式的轻狂,没想到34年后倒在下一代人身上美梦成真!
那么,我国高山宇宙线研究砥砺前行的历史轨迹,EAS(广延大气簇射)实验和γ天文研究在我国落地开花的陈年往事,是时候让正堪大任的我国第三代宇宙线学者知晓了解了。只有同时具有国际观和历史观(即横向和纵向视野),才能认准方向不动摇,有情怀有使命地把由王淦昌、赵忠尧、张文裕、肖健等前辈大师开创的我国宇宙线研究的优良传统,继承下去和发扬光大。
二、中国宇宙线研究的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的方向大辩论
我国宇宙线研究的起点不低。1951年在近代物理所时就成立了以王淦昌和肖健为正副组长的宇宙线研究组。1954年在肖先生主持下建成了云南落雪观测站(3200米),用赵忠尧、王淦昌自美国带回来的50cm多板云雾室和自制的30cm磁云雾室寻找“奇异粒子”,观测电磁簇射,取得过许多高水平结果。1958年,作为献礼项目启动了当时世界上最大型的一个由上、中、下三个大云室(上云室数水珠测游离,中磁云室测曲率定动量,下多板室观测次粒子行为)组成的云雾室实验系统的二机部“311工程”,选址云南东川“222”地区一山头建站(即后来的云南站)。拟在数十GeV(109eV)能区开展高能核作用研究。工程因“三年困难时期”的暂时下马,拖到1965年才建成;不料又遇“文化大革命”的岁月蹉跎,眼睁睁看着加速器占领了它的工作能区。国际惯例,一旦加速器进入,宇宙线就应把此能区的粒子物理研究让位给加速器实验,自己往更高能区迁移。伴随着的是大量人员的自动转移(向基于加速器的高能物理实验),或者课题转向宇宙线天文。文革结束后,中国宇宙线研究还干不干,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严肃地摆在了每个宇宙线研究者面前。

图1 原子能所在云南东川海拔3200米的宇宙线实验“云南站”
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当时的室主任霍安祥先生作了件最正确的事:发扬科学民主,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全室人员开展中国宇宙线研究前途、方向、手段的大辩论,形成了一段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局面。最先找准了路子的李惕碚和任敬儒等,分别转向了空间X射线天文和高山乳胶室实验(UHE核作用);我初期也调研过空间非热辐射,后来则把目光聚焦于了EAS。
为什么是EAS呢?当时能够得着TeV(1012eV)以上能区的宇宙线观测手段只有三个:地下磁谱仪,高山乳胶室和地面EAS阵列。前者已达极限,会很快退出舞台。高山乳胶室在当时风头正盛,然而这种没有时间信息的被动式无源探测器,虽然简单廉价,不需人员值守,但其后期处理和事例重建的手工化严重限制着它的规模;看着加速器实验技术的日益现代化,将有多少愿意成天与显微镜作伴的年轻人呢?而EAS阵列可覆盖UHE(当时概念1014eV~1017eV)甚至此上的EHE(极高能)区,如果阵列大到10平方千米以上,1020eV的宇宙线粒子也是可以捕捉到的。关键还在于它属于与加速器实验同型的“计数器实验”,便于规模化、自动化和数据处理的计算机化,从而可成为将宇宙线实验从原先的“小农经济”式转变为“现代化大生产”式的合适手段。于是,以EAS为手段,以超高能作用特征和超高能宇宙线原初成份为探测目标的想法基本形成。然而,习惯于按领导分配干活的我等,哪里知道它所需的物资技术条件与当时我国的工业水平和经济实力差距之巨,不知不觉把自己逼进了一条孤独的登山单行道。
三、怀柔练兵
1980~1981年春,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宇宙线研究所参与Akeno(明野)阵列实验并分析EAS纵向发展时,遇到一大困惑。在1981年日本物理学会广岛春季会议上,我报告中给出的明野过渡曲线,与Suga(菅浩一)先生报告的Chacaltaya结果怎么也难以协调,为此Suga先生还作出了在超高能存在某种新粒子的解释。Suga先生是日本EAS界的元老、Chacaltaya国际观测站创始人。位于玻利维亚的Chacaltaya观测站,海拔5200米,按说垂直入射的PeV级宇宙线粒子引发的EAS正好在此高度达到发展极大,因而Size(总粒子数)最大,发展涨落最小,处于最佳测量位置;而明野阵列虽然只有900米海拔,却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且完善的阵列。究竟是哪家实验的错还是真发现了什么新物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一天中午在食堂遇到刚从西藏归来的汤田利典(T.Yuda,当时是该所乳胶室部副主任和中日甘巴拉山乳胶室合作日方负责人),他说进藏期间去地热基地羊八井观光,见那海拔4300米的地方十分宽阔平坦,还有地热电厂,是你们做EAS实验的好地方。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回国造一个标准的EAS阵列从海平面一直作到西藏去的想法就此产生。
1981年5月我回到所里,即找肖健先生(其时他已脱离宇宙线,在加速器那边带研究生)请教。肖先生把我的困惑归结为宇宙线实验数据的“归一化困难”,源于各家各自为政高度独立式的运作。讨论到源于原初成分和作用模型的相互纠缠的宇宙线实验结果解释上的多义性,肖先生说没有什么好办法,需要长期努力、逐步逼近。我的计划他很支持,但认为困难很大。他说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想搞EAS,也幸亏没搞,否则在那时的技术条件下结果难料,文革时就更难交代了。因此一再问我有没有“铁杆支持者”。说他主持311工程时,那么大的班子,还打着二机部的核旗号(重设备都通过海运先到越南再转小火车入滇,)都那么困难,你到西藏建站哪那么容易?怕他担心,我硬着头皮说“有铁杆”。其实,当我兴冲冲带着方案回国时,本以为可说服室里采纳我的方案,(按以前惯例)自上而下分配经费、组织人员加以实施。不料老皇历已经作废,室里不设统一大项目,众多百花齐放小课题已将现有的经费、人员分光,我就成了个“光杆”。
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居然敢从零开始。1981年8月我以“EAS纵向发展的统一观测”为题申请所里基金,因学术委员会(肖先生时任物理委员会主任)含许多外籍委员难以开会,拖到1983年才获得一笔20多万元的启动基金。其间,我们并未坐等,而是利用镰田先生(Kamada,时任东大宇宙线所空气簇射部主任、东大明野观测所所长)赠送的三块旧塑料闪烁体和自费带回来的部分集成电路块,作探测器和相关电子线路的预先研究,稍有进展就请肖先生来看。后又在张文裕、肖健先生推荐下,获得了院基金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前身)(50万元)经费支持,正式开始了怀柔阵列的建造工程。1986年在主楼楼顶建成和试运行了一个由16个探测器组成的全功能EAS小阵列;1987年在怀柔院绿化基地某地块(位于现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园内)以53个1/4平米闪烁探测器(其中9个有快时间功能)建成了一个覆盖面积11000平米的基础型EAS阵列。通过全自力更生的建造过程和其后的EAS现象学观测研究,相关人员对EAS现象特征、簇射结构和实验方法有了必要的具体认识。1990年前,先后有17人参与过怀柔阵列的工作,我国第一支小小的EAS队伍至此形成。现LAHHSO领导人曹臻也作为研究生在此接受过EAS的洗礼。十分遗憾的是,肖健先生因病于1984年过早仙逝了,没能亲眼看到EAS研究在祖国落地的这蹒跚第一步。

图2 北京怀柔EAS阵列,在国内首次获得超高能宇宙线能谱
与此同时进藏准备也在加紧进行,只是有两件事使得须对原有设想做些修改。一是在事无巨细的建站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限于当时国内落后的电子工业基础,以全自力更生方式,是能够建成一个具基本功能的EAS阵列,但不可能是个国际上先进、能愉快胜任高山野外环境下长期持续运行的阵列。这不仅在于国产集成电路和计算机的短缺,仅从在调试中不时出现因接插件(品种数量极多)接触不良导致的麻烦就有深切感触。所以怀柔阵列的功能就是练兵,上山还需突破全自力更生的思想框架另建新阵。二是1983年西德Kiel大学Allkofer领导的EAS实验组宣布,他们在1PeV~20PeV区间以4.4σ的显著水平观测到了来自天鹅座-X3(Cyg-X3)的超出,亮度竟然高达3×1038erg/sec。这不等于他们发现了UHE-γ源,进而宇宙线粒子源了吗?这个后来被我们证实为不实的报道,立即引发了国际上寻找UHE-γ源的十年热潮,相继出现了十来个找源阵列,就连诺贝尔奖得主J.W.Cronin也自加速器转向宇宙线,领导芝加哥-密执安大学合作组在Utah筹建大面积的CASA_MIA阵列。因而,γ源寻找必须被列入西藏计划并成为首要目标,同时,国际合作也成为了必然选择。
四、《西藏计划》的筹备
在怀柔阵列建造刚上轨道的1984年4月11~30日,我完成了西藏选点考察,选中羊八井,并与羊八井地热科研所和地热开发公司达成(支持建站的)合作意向书。5月17日向室里、所里提交《西藏考察报告》并要求进藏建站。开始室里不同意,主张回云南站去建。僵持到6月13日,我向室领导作出“责任自负、经费自筹”的保证后,获得默认课题自主。刚经历过云南站撤站善后麻烦的院、所相关领导也十分担心我们会不会又在西藏弄个难以善后的烂摊子。毕竟,为让云南省消化几十号原云南站的滇籍职工,院里出钱在昆明翠湖招待所修了栋楼房相送才算摆平的事还记忆犹新。于是我又保证西藏站一个行政人员都不用,全由科研人员代劳。没想到这一保证竟成了羊八井的光荣传统,30年来,一直没占所里一名人员编制,只用了3名“临时工”,成了我院众多野外台站中唯一一个没有行政人员也没有车辆(2005年,ARGO-YBJ建设过程中院里才送来一台)的台站。
改革开放使我们思路大开、胆量倍增。基于羊八井独特的高海拔地理条件所蕴藏的物理优势开展国际合作,调动国际资源成了我们不二的选择。利用国际宇宙线乳胶室专业组1986年要在北京(丰台的京丰宾馆)召开《宇宙线超高能作用国际研讨会》之机,在大会秘书处丁林垲的帮助下,塞进了个《Tibet Project Workshop》,特意邀请了一批国际宇宙线专家(如美国Cygnus组负责人Yohd,犹他的陆震,芝加哥的Hassen,日本的Suga,Yuda,意大利的D’Ettorre等)与会。高海拔的物理好处一说即明,能让这些好处变现的羊八井地理条件(4300米高海拔、距拉萨仅90千米,平坦开阔的地形,温和少雪的气候,常年通畅的交通,与电厂、邮局和藏村为邻)才是吸引这些内行的武器。会上顺利达成了中、日、意三方合作意向;会后Yohd在顺访高能所时又来给我说,待他在Los Alamos的CYGNUS实验告一段落即来参加羊八井合作,还讨论了用玻璃钢作光导箱并在中国工厂规模生产的可能性。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没有邀请“发现”UHE-γ源的Kiel大学组加入合作呢?事实上,他们比我们更积极。Allkofer已通过当时在该组作访问学者的姜映琳联系访华。我猜得出他访华的真实目的,事先与陆柱国(新上任的宇宙线室主任)合谋去云南,(在云南大学高晓宇、杨自天的合作下)在昆明远郊的梁王山选好了一个2800米的站址,准备在此和云南大学一起与他合作。然而他对此毫无兴趣,在访问怀柔站和在友谊宾馆请我喝咖啡时,他一再要求去西藏看看,我都以办不了进藏许可证为由婉拒了。我想他一定也猜得出我的心思:“你要是在Kiel都能找到,那我把怀柔阵搬上去也能找到了”。后来不久,听说他不幸病逝时还真觉得有些对不住他。
丰台会议后,日方决定以参与甘巴拉合作的原班人马参加羊八井合作,并积极在乘鞍山开展小项目,训练年轻人入行EAS。意方也组成了个小组,按分工着手试验他们的强项SQS管(自淬灭流光管,希望能用它做大面积μ子探测器)能否在不流气状态下工作。然而中方不能立项,谈好的国际合作又怎能启动呢?情急之下,我附着我国天文界元老王绶琯和宇宙线界元老霍秉泉先生的亲笔鼓励信,于11月8日越级给孙鸿烈副院长写信,没有回音。逾年,1987年2月21日,我的《建立西藏宇宙线观测站的建议》及其补充说明终经新任所长叶铭汉,按程序正式向院里上报。然而,在中方的漫长等待期间,美国Yohd开始了他的MILAGRO新计划,D’Ettorre等也投向了在Gran Sasso山顶的EAS-TOP Array项目。
五、中日合作AS-γ实验与中意合作ARGO阵列
就在这西藏计划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1988年3月,Torri(鸟居祥二)作为甘巴拉乳胶室中日合作组成员来京处理乳胶片时,带来了汤田申请到数千万日元科学基金的消息。室里立刻行动了起来,宣布成立以霍安详为首的“羊八井合作筹备小组”。4月12~24日,我与研究生戴宏跃即进藏实施了第二次羊八井考察,确定了现在的羊八井观测站阵址。5月9日,我提交正式报告,叶所长欣然决定将处理云南站剩余金属材料所得的20万元拔作我组羊八井建站专款。7月20~26日,日方坂田通德(Sakada,甲南大学教授,有EAS经历)来京并访问怀柔站,协调并敲定了羊八井起步阵列方案。从此,西藏计划以中日羊八井双边合作方式正式启程。
1989年5月,力京进藏,羊八井观测站破土动工。同时我与王辉赴东京参与日方设备的系统检验,以便装箱海运,准备秋天在羊八井组织安装调试,争取达成年内运行的愿想。不幸,“天安门事件”发生,国际上的过度反应几乎使我们的计划陷于绝境。但是,我们始终坚信党和政府能很快稳定国内局势,进藏决心没动摇。10月,局势稍有好转,我急与袁鹏赶赴羊八井作建站前的准备。11月,中日双方团队齐聚羊八井(日方由Kasahara(笠原克昌)带队),在寒冷的冬季野外作业,建成了一个由45个同时具有粒子密度和快时间测量功能的0.5平米探测器,以15米间距布成的EAS阵列。在1990年元月10日开始试运行这一天,有西藏自治区领导和当地人士前来祝贺,我们就趁机宣布了羊八井观测站的成立。1990年3月初,高能所、西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云南大学的一些对西藏计划感兴趣的学者,在成都聚会,组织γ天文讲座,协商成立了“羊八井中日合作中方委员会”(随后又有山东大学和郑州大学参加),确定了羊八井观测站由合作委自主管理的运作模式。
1990年6月,在年初运行的阵列四周加了16个0.25平米探测器(乘鞍山旧品),AS-γ一期阵列建成并投入正式观测运行。
到1992年初AS-γ积累了6亿多事例,据此在10TeV能区并未看到当时已知的高能γ源Crab Nebula,Cygnus-X3,Hercules-X1和活动星系核方向有任何具有统计意义的超出,测得的流强上限也很低,基本上与电子起源的SSC模型的预期一致。这就否定了1983年Kiel组的超高能γ源“发现”,并给我们以这样的导向:要实现正确的探测,须设法降低阵列的观测阈能,在甚高能与大气切伦科夫光望远镜(AICT)优势互补地展开工作(阵列的宽视场、全日制补充望远镜的指向跟踪和只能在晴朗无月夜晚开机的弱点)。
1994年,对AS-γ阵列进行了二期扩建:探测器增至185个,覆盖36900平米。同年12月,《首次西藏宇宙线物理国际研讨会》在拉萨成功举行,与会的国际知名学者甚众。至此,羊八井观测站被国际同行广泛承认和期待,同时也在国内知名。国家基金委数理学部主任王鼎盛一行访问羊八井后,我们顺利申请到70万元资助(与室里别的课题分享)用于运行维护,阵列扩大的资金还主要靠日方。在怎样进行三期扩建上,与日方曾有过一些分歧:我意在扩大加密阵列,汤田计划上些乳胶室与阵列进行联合实验。在1996年4月杭州工作会议上,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二者都进行但缩小规模的现实方案(只上80平米乳胶室和将没有时间信息的它与具体的EAS事件联系起来所需的80平米Burst探测器)。我们能够理解汤田的苦衷:他作为宇宙线所乳胶室部主任去申请经费,课题完全与乳胶室不沾边怎么好向他们文部省交代?但也深切感觉到,自己经费拮据又总想主导进程,的确为难。
1996年11月,在探测器以15米间距覆盖36900平米的二期阵列中,我们将间距7.5米的加密区用109个探测器扩大到了5175平米,探测阈能降至3TeV。利用自1996年11月至1999年5月积累的17亿EAS事例,以5.5σ超出探测到了蟹状星云的在>3TeV的γ发射。这是国际上EAS阵列的首次成功的γ源正探测。阈能的降低和数据的积累,也使月影偏离和宇宙线非各向同性度等研究得以开展。
在专注γ源寻找的同时,也没完全忘记西藏计划的初衷(γ天文、膝区物理和日地空间环境),1988年自日本理化所引进了中子监测器和中子望远镜各一套。2000年11月,在昆明滇池边举行了“中日合作第二次工作会议”,总结成绩,讨论发展。那是我在任时主持的最后一次中日双边会,几乎所有合作单位的主要成员悉数到会,友谊团结的气氛洋溢于会场内外。
至于中意合作,自1986秋在北京分手后,D’Ettorre及几个同伴如约进行了一段SQS管由流气改封闭的试验之后,因我方迟迟没动静而转投本国的EAS-TOP项目去了,中间有几年没有联系,直到1993年在加拿大加尔加里国际宇宙线会议上才相遇。交谈中,得知意大利加速器实验中出现了一种新型探测器RPC(阻性板室),结构简单(室薄而无丝)、成本便宜(塑料壳体),可灵活布置感应输出,有在宇宙线实验中使用的前景。使我立刻想起了当年参观日本乘鞍山阵列“火花室地毯”的情景。在一个四壁漆黑的房间里,地板上密密麻麻地铺着许多玻璃火花室。工作时关了灯,眼前一片黑暗,EAS触发信号一来,一些火花室突然闪光放电伴着噼噼啪啪的声响,屋脚高架上的几台照相机同时打开快门拍照,其壮观景象,真是摄人心魄。然而问题不在于火花室的昂贵,更在于它并非计数器型而是径迹型探测器,只能以统一触发、分别记录、事后拼接的方式进行事例重建,过程复杂、效率低下,不可能真正用于EAS粒子心结构的测量。那么,RPC会不会就是建造大面积“地毯”的好材料呢?如果是,就可能把传统的多点取样式阵列发展为“全覆盖式阵列”,将取样比自AS-γ的1%(已是当时国际最高)提高至90%以上,可把阈能降至100GeV能区,从而使γ源寻找能扩到红移值Z~1的河外空间,也能使宇宙线月影观测变得更容易,甚至使质子反质子比测量成为可能。在将来的精细复合型阵列中心,它更能充当芯区地毯去精细测量UHE-EAS芯区的粒子分布精细结构,十分有利于“膝区物理”的研究。问题在于,这种RPC的感应输出能否同时满足我们对快时间响应和大动态粒子密度测量的要求。
1994年冬,耗时2星期实现了意大利访问之旅。我先后访问了Pisa大学、莱彻大学和罗马二大的INFN分部,造访了RPC发明者Santonico的家及其RPC实验室,达成合作意向。为慎重起见,商定先合作在羊八井作个小型RPC现场试验。经过一番准备,1997年冬至次年春,50平米RPC的羊八井现场试验取得满意效果,双方决意分别申请经费实施羊八井地毯式阵列计划。因为“地毯”必须建在薄屋顶的少遮挡物质的大厅之内,中方的开支也会很巨大,须挤进中科院九五计划重大项目并同时向基金委和科技部集资才能解决。在得知它们三家有意联合支持后,1998年11月30至12月3日,《中意羊八井ARGO合作首次工作会议》在高能所举行,名为《Joint Statement Concerning ARGO-YBJ》的正式合作文件得以签署(ARGO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遍身长眼、永不睡觉的护宝怪兽,比喻地毯式阵列的宽视场全覆盖)。实际上,我们的项目申请是1999年12月4日才在王乃彦先生主持的院、部、委联合评审会上正式通过(3400万元)。在稍前的9月份,我们已先期获得羊八井镇允许,在AS-γ阵列东侧圈下了一块200米见方的用地。2000年4月,在高能所开具延期付款银行担保证明后,万平米ARGO大厅破土动工。2001年6月4日,在大厅落成并局部安装开始之时,举行了有白春礼副院长、科技部马副部长、基金委副主任、自治区首长和意大利INFN主席、驻华大使等贵宾出席的盛大落成典礼,开启了规模化的设备安装调试过程。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把ARGO纳入中日意三方合作框架而搞成了两个独立的合作呢?是日方不愿意,不便勉强。为什么那么急?你不见HE区的空间探测器已找到百多个,AICT们也已确认了其中~10个为VHE-γ源,唯独EAS阵列只测到1个Crab(后来,羊八井AS-γ阵列还探测到过1997年Mrk-501及2000年1月Mrk-421的flare式γ射线爆发),能不着急?

图3 西藏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图中白色的是中日合作AS-γ阵列的探测器,
蓝色屋顶的大厅内安装了中意合作ARGO地毯式探测器阵列
以后的事,现役的很多人已有亲历,不用赘述。年届退休,倒有两件想办而未能办的事可以提一提。一是曾在威海会议上报告过的拟以数千万元资金,以ARGO地毯为中心建个“Supper Complex ASArray”,以便在现有课题之外同时兼顾膝区物理和UHE-γ天文。另一个是与德国合作建个高海拔巨型大气切伦科夫光望远镜阵列(4台25-30米口径的AICT,100米间距布列),意在以~5GeV阈能把观测视界扩至Z~3的深空,发现更多的河外γ源,监测短时标变源,捕捉爆发事件。为了准备复合阵列,我自意大利要来了数个集装箱的GRANSASSO地下实验退役SQS管以备μ子探测器所需;为巨型AICT计划,应邀于2002年9月访德,与海德堡核研所所长Volk,HESS实验领军人Hofmann及在前苏联就认识的Aharonian等共同谋划;还为此选好了羊八井谷地西端距现观测站19公里某处的站址。此后均因故不了了之。
可以看出,当年我与许多同伴花了20多年时间,急冲冲、忙慌慌,以一系列具体科研小课题为名争取经费,将设备规模和种类有如“穷人家小孩的衣裳”似的“越接越长”,实际上做的只是一件事:构筑我国高海拔宇宙线和γ天文的实验基础。从而走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徬徨,延续了地面宇宙线实验的烟火,完成了我国宇宙线研究自手工化的云雾室、乳胶室时代向数字化、规模化的现代化实验的转变;搭建了一个国际性实验平台,让年轻人能在国际舞台上摔打成长。在其后卢红、胡红波、曹臻和黄晶主事期间,羊八井平台更培养了一批青年才俊,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奠定了我国宇宙线研究文脉永续、前景光明的良好基础。
通过对这段业已尘封的个人亲历的往事回忆,有几点感想愿与年轻人分享:
1)科研事业的成败当然离不开物质、经济等外部条件,但一个主观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从事科研不要太功利,要有目标、有理想、有情怀。它们是你超越障碍、抗拒诱惑、不忘初衷、坚持到底的内在力量。
2)没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国家的日益强大,《西藏计划》就很难避免骑虎难下,真落得个需要别人来善后的下场。试想,要是西藏的道路一直是“搓板路”,西藏的通讯一直差到连羊八井到拉萨的民用电话线都没有,进藏的飞机票有时需半个月的等待,如何能支撑这样现代化国际化的高山实验?伴随着祖国日渐强大的脚步,我们见证了兰青拉光缆线的开通,青藏铁路的通车,目睹拉萨从一个能源市场卖牛粪和劈柴的古老城镇一跃成为现代化都市的大变身。也经历过改革初期因海关不允许进口国内已能生产的机电设备,和外国人带进来的仪器必须随身带走的规定,我和汤田合谋在设备名称上弄假,并让他给我开“赠送函”(东京大学居然很配合,还盖章)等开放初期带来的尴尬。若非改革开放,没有国际合作,仅靠几台“386”微机,我们怎么储存和处理那么大量的原始数据?诚然,改革开放也曾给我们带来过一点麻烦:出国大潮曾不断卷走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就连合作单位送来的大多数研究生也以羊八井为跳板去了外国。也有回来的,如查敏和曹臻等。正因为国力日盛,我们才不愁后继无人;也因国力增强,国家才能以3400万元巨款支持ARGO建设。
3)宇宙线是宇宙的使者,同时携带着宇观世界、微观世界和日地空间环境的宝贵信息;而我们的EAS阵列又是宽视场、全日制、可长期连续运行的固定大装置,且以γ天文为主要课题,这样的观测站就具有天文台的性质。当年我一直在向院基础局、资环局陈述这个观念,希望能给羊八井站以天文台待遇,有常年运行费和维护人员编制,以保障其长期运行(靠课题费维持则只能让观测站伴随课题经费的断档而衰亡),并作为全国共同利用的基础设施对外开放。
写到最后,脑海里不由浮现出一段张文裕先生的画面。(文革后期,我和何景棠等曾与张先生共一个办公室。)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小组会上讲到一个故事:一次在印度召开的国际宇宙线会议上(没有中国代表与会),有人向(解放初曾作为专家来过我国的)苏联著名的宇宙线专家德布罗金问及中国的宇宙线研究情况,他不说话,而在座位上举起双手比了个“0”字。每说到此事,张先生都异常气愤,满脸红涨、口齿结巴地反复说:“我们怎么是零呢!”到2011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32届国际宇宙线大会之后,在去年羊八井AS-γ阵列测到Crab的450TeVγ射线,如今LHAASO更将河内多个VHE-γ源的能谱一直延伸到超高能能区,UHE-γ天文窗口即将真正打开之际,我们已可告慰张文裕先生在天之灵,再不会有人说中国宇宙线研究是零了。也告慰在中国最先主张EAS实验并亲身帮助启动了怀柔阵列研制的肖健先生:你所期待的高海拔EAS研究已在祖国生根开花,硕果可期。
(文章版权《现代物理知识》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