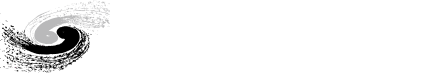(根据张文裕先生1986年5-6月口述,高能所丁林垲研究员整理)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曾透彻地阐述了“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认识论原理。前几年党中央又进一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提法也是对科学发展史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此外,我们党又一贯倡导学习唯物辩证法,倡导认真严肃、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所有这些对科学发展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是实践。由于历史的影响不同,在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在我国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的。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从隋朝初期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从世袭制到开科取仕的科举制,在当时是个进步,但科举制的内容主要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至于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极少研究的。科举制持续了一千二百多年,直到清朝末年才结束,所产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是几十年革命就能扫除的。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要研究“物”,必需变革“物”,并观测其变革后的反应。以这些反应的现象作依据,经思维加工而推出结论。全部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的内容,包括物理事实和由事实推出的规律,都是由科学实验得出来而不是由脑子臆造出来的。西方科学界流行着这种看法:改理论迁就实验,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要否定一个实验,必须有新的、更准确的实验结果。他们普遍承认科学实验是理论的源泉,是自然科学的根本,也是工程技术的基础。反映在教育上,培养学生也是从科学实验着手,把重点放在实验上,非常重视实验课,不管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成为理论家或实验家。据说这种教育方法在欧洲是由麦克斯韦(J.C.Maxwell),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第一任主任)亲自奠定基础的,他非常强调要学生重复别人的实验。像麦克斯韦这样的大理论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物”,而不是“数”(数学符号)。
我从二十岁出头就开始从事科学研究。但是对上述西方科学界的看法,特别是对科学实验的重要性,是十年之后在普林斯顿(Princeton)工作时才开始认识到的。到把这种看法变成了习惯,恐怕还要经历几次摔跤的实践经验,才能真正把握住。
在这本选著里,主要汇集了我在燕京大学、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和普林斯顿大学亨利实验室这三个地方的工作。这三个地方有一定的联系,在教学与科研的风格上有类似的传统。燕京是美国人办的一所典型的教会学校,以美国大学作为规范和模拟。美国的大学在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又是跟普林斯顿学的。普林斯顿被认为是美国物理学的中心。但是,普林斯顿的传统,又是由卡文迪什来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在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特别强调科学实验。
我将结合选著中涉及的工作,回忆我的一些经历,同时回顾一下我两次回国的不同感受;最后,谈谈我对教学与科研的一些体会。
一、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以美国式的大学作为规范和模拟的一所大学。在物理学的教学中强调实验,在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中以科学实验为主。这所大学有一定的实验设备,由一位教授负责实验课,配合若干位助教,具体讲解每一个实验的原理、要求和作法,数据怎样收集,怎样做成一个实验报告,并看着学生作实验。实验报告要经过助教签字,特别注意有效数字的取舍和误差的处理,不合格的要退回修改(英文叫 return for correction)。常常一个报告要退回修改二、三次方被接受。分数不及格要补考,或者不给学分。对每一门学科(如光学、电磁学、力学、原子物理、核物理等),基本上每星期有三小时授课(往往含有实验演示)和半天相应的实验课。实验课还设有几台机床,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去做一些另件。这些作法都与美国的办法相同,只是程度和水平可能有些差异。
这一段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科学实验的基本功和工作态度的训练,物理问题的意义不是主要的。强调练习难于驾驭的仪器,如迈克孙干涉仪、康普顿静电仪等,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凡是燕京出身的都比较清楚,物理系的教师们,如谢玉铭、杨盖卿、孟昭英、诸圣麟、威廉曼、安得逊等先生,对系的建设、对学生的培养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我个人来说,谢玉铭先生用的工夫最多。他实验很灵,光学、近代物理都是他教的。研究生的题目,多由训练的角度挑选。我与谢玉铭教授是同乡,接触比较多。没有他的关心、鼓励,恐怕不会有我的今天。当然还有其他前辈,如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严济慈、杨石先、姜立夫、赵忠尧等先生,我经常回忆起他们对我学业成长的关心和帮助。其中来往时间最长和最密切的要算赵忠尧先生。我在一九三O年左右就认识他。到剑桥后我们经常通信,他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帮助。
燕京的另一个特点是举办seminar(讨论会),每星期一次,每次一或二个人讲,接着讨论,共用半天。主要是由学生讲国际近况,有时报告自己的工作。当时燕京讲课用英文,seminar也是用英文。这样一边学英文,一边学物理。后来我到卡文迪什和普林斯顿,都有这种作法。
二、英国剑桥大学
我是一九三四年考上第三届英国庚款到剑桥大学留学的。一九三五年夏天到剑桥,按规定为期三年,若有必要可延长至四年。到剑桥后,我在该校的卡文迪什(Cavendish)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实验室主任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卢瑟福(E.Rutherford),也是我的导师。他继承了他的三位前任麦克斯韦(J.C.Maxwell),瑞利(J.w.Strutt),汤普森(J.J.Thompson)的传统并发扬光大,把卡文迪什实验室办成一个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近代物理研究基地。
我在卡文迪什实验室时,该实验室共有三个大组。
第一个是埃里斯(C.D.Ellis)组,利用铀和镭做的α、β放射源进行天然放射性的研究。埃里斯本人是研究β放射性的,β比α复杂。他发现从放射源出来的β射线有线谱,也有连续谱。线谱是从核外出来的(轨道电子吸收核内出来的γ并放出电子),连续谱才是从核内出来的。泡利(W.E.Pauli)就是根据他的工作,分析了三体衰变,提出了中微于假设。泡利对埃里斯的工作很赞赏,说他应该得诺贝尔奖金。李国鼎在剑桥就是跟埃里斯作β衰变的。
第二个大组是考克饶夫(J.D. Cockcroft)组。这个组围绕一九三二年自造的 500 KeV的Cockcroft-Walton倍加器作核物理工作。后来委托荷兰的菲利浦(PhiliPs)公司造了一台更大的(能量为 l.25 MeV)。
第三个大组由卢瑟福和奥利芬(M.L.E.OliPhant)等组成,人数不多,研究有关中子的问题。
我一开始在埃里斯组工作。可以说埃里斯是我在核物理和技术方面的启蒙老师。名义上,我的导师是卢瑟福,但真正的导师是他。我在这个组的工作是用α粒子轰击轻元素如Al、Mg等,研究所形成的放射性同位素的产额与α粒子能量的关系,由此来研究原子核的结构。当时对原子核的结构还不很清楚。卢瑟福和玻尔(N.Bohr)有二十几年的师生和合作关系,提出了原子模型。玻尔提出原子核的液滴模型后,我们就想用α粒子作探针去研究核的结构。当时已经认识到不同能量的α粒子都可以进入核,但有选择,有的能量进去的多一些(即有共振现象),表明核不是光滑的,不是一个点,而是有大小的,有连续性;不是一个刚球,而是一个软的东西。
埃里斯对工作很负责,对学生很关心。他亲自教我制备放射源的方法。为了制备氡放射源,清早四、五点就开始工作,他都来帮助我。他教我如何写文章,每篇文章都经他修改后才送给卢瑟福审阅,然后再送出去。我们相处得很好,后来他要到伦敦大学当教授,建议我跟他一块去。他去后,我就转到考克饶夫组了。
一九七二年,我们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时,听说埃里斯还健在,可惜没有机会看到他。
我在考克饶夫组参加过两个小组的两项工作。其中一个小组由刘易斯(W.B.Lewis)领导,用倍加器产生放射性的8Li和8Be,研究它们的衰变机制。8Li的半寿命比较长,接近一秒。8Be是一个激发态,退回基态时放出两个α粒子。测量α的能谱,发现它是一个连续谱,由此判断激发态的分布很宽,半寿命仅约10-16秒。另一个小组是哥德哈伯(M.Goldhaber)组,由他、我和一个日本人,叫嵯峨根的,共三个人组成,利用倍加器产生的γ和快中子去打不同的元素,形成许多种放射性元素,观察(γ,n)(γ,2n),和16O(n,p)16N等过程。这些过程现在早已熟悉,可在当时还完全不清楚,是头一次研究。其中,中子和16O的反应在反应堆的设计中要非常小心地考虑,因为冷却水里有氧,产生出来的16N有放射性。
刘易斯和哥德哈伯都还健在,都还有来往。刘易斯比我大一两岁,搞电子学和探测器的能力都很强。他后来担任加拿大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一九七二年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时,我们住在多伦多中国大使馆。他得知后,亲自驱车从Chalkriver赶到多伦多找我。三十几年末见面了,大家非常高兴,畅谈了一个晚上,谈完他又开车回去。
哥德哈伯后来到美国当教授,作过一任布鲁克海文(Brookhaven)高能所的所长,和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曾来中国访问过。
卡文迪什实验室的研究方向、领域,以及每年的题目都是主任和几位副主任讨论决定的。他们还经常与研究生和其他人员商量讨论,民主风气很浓。作为实验室主任,卢瑟福很关心研究的进展,每个星期总要到各个组了解情况,询问遇到了什么问题并亲自想办法。他平易近人。每个月邀请我们到他家里作客,他的夫人是农村人出身,非常朴实、善良,待人热情。
一九三七年,卢瑟福去伦敦作手术,不幸逝世。他的逝世是科学界的巨大损失。噩耗传来,卡文迪什的气氛立即改变。从伦敦举行的隆重的葬礼中可以看到他的影响。同我去伦敦参加葬礼回来的同事们都惊奇地说,没想到我们有这么伟大的人物。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南京失陷,日寇大屠杀,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英国报纸登载的很详细。在剑桥,国内去的几个同学天天用很多时间看报,看完就讨论,完全没有心绪作研究或学习,都想回国参加抗日。跟别的同学一样,我写了信给英庚款董事会,申请提前回国参加抗日。董事长朱家铧回信说,回国可以,但必须完成学业,得到博士学位才予以考虑。于是我向研究生院提出了提前考试的要求。
卢瑟福对我要求提前考试,提前回国很不以为然。大约六月初的一天他到实验室来看我,说:“…听说你要回中国,不要这样。我想中国应忍着,等以后强大再说。硬打牺牲太大。至于你,还是留在这里继续作研究好。这是我最关心的事。你若有经济困难,我可以想办法。”我立刻回答:“经济上一点困难也没有”。至于他其他的话,我没吭声,但心里反感,不愿意听。不久,他就去伦敦治病了。没想到我们的这次谈话竟成了最后一次。
经申请后,剑桥研究院同意我提前考试,由考克饶夫主考。事先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总认为这种考试主要是考论文,把已发表的论文综合一下就成为博士论文。心里想,对我所作的论文我比谁都清楚得多。
结果考论文没几分钟就过去了,然后转向考基础课。大部分问题涉及基础实验课内容,如:一束光穿过一条狭缝或两条狭缝,在后边屏上形成什么样的花纹?怎样用图大致表示光的极化、绕射?用牛顿环怎样求波长?还有低温等等问题。我回答得很不完美,连自己也很不满意。当时很激动,算了!不考就回国吧!
考克饶夫很平静地耐心规劝我:“还是准备再考吧!这结业考试对你有好处。你不是本校毕业的,是中国第一个在这里考博士学位的人。你的研究工作没有问题,但我们对你过去在中国训练的情况并不清楚。考核一个人的水平,考试是个好方法。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考试的国家,我们英国的文官考试(exam)就是从中国学来的。听说中国别的同学也不重视考试,李国鼎就跑掉了。我考虑还是请你再准备一下,用三个月功夫,再考一下好不好?”我看他这么诚恳,只好答应了。
到一九三八年春我再次参加考试。三个月间我把过去本科学的基础课,特别是实验基础课,彻底复习了一遍。复习中参考、学习了剑桥本科的学习内容。虽然燕京是强调实验的,但仍不够,要求仍不一样。这次考了约一个钟头,考克饶夫就说可以了:“You are through”!这样考试就通过了。
颁发博士证书的典礼要到夏天和别人一块进行。院方要我先准备典礼所需要的礼仪,并进行预演。
到七月领学位证书还有三、四个月。我就利用这个时间为回国后的工作做些准备。由李国鼎与国内联系,以防空学校校长黄振球的名义介绍我到柏林 AEG工厂学习探照灯技术(但要自费)。我在AEG公司实习了一段时间,七月初回到剑桥参加颁发博士证书典礼后,又回到AEG厂继续实习。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我回到剑桥。结束了四年的留英生涯,抱着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十一月初我离开剑桥经马赛坐船至河内,回到昆明,而后到贵阳。回国后方得知防空学校已搬至桂林。
促使我提前回国的另一个原因是王承书已好久未给我来信,下落不明,使我放心不下。这时我们已经要好五、六年。回国后知道她已逃到贵阳,在湘雅医学院教书。
我在贵阳等了一个多月,才接到黄振球回信说:现在情形很不安定,你可另外高就。
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亨利(J.Henry)物理实验室
一九四三年,我由西南联大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帕尔麦(Palmer)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是美国历史最长的实验室,(几年以前已改名叫亨利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继承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传统,它的物理教学和科研的精神、办法,与卡文迪什很相似。有一个时期,本身的教师约四分之三在卡文迪什作过研究。当时的研究教授莱登伯(R.Ladenberg)和前任研究教授康普顿(A.H.Compton)都在剑桥卡文迪什工作过。因此,在教学和科研中都很强调科学实验的重要性。美国老一辈著名的物理学家大多是由这个实验室出身的。上面提到的康普顿的哥哥(K.T.ComPton)也是普林斯顿的。与卡文迪什相同,这个实验室不收本校毕业生为研究生。
我去普林斯顿,与卡文迪什有点关系。我在剑桥时,有一年莱登伯到卡文迪什参观,卢瑟福介绍我和他认识。一九四三年初,那时局势很乱没有多少书可教,我由西南联大写信给他,说希望到普林斯顿工作。他当时已转作国防工作了,研究基本上停止了,但在普林斯顿还有一点工作。他还记得我,很快回信叫我去。
与此同时,加州理工学院(C.I.T.)的院长密立根(R.A.Milligan)教授要周培源、孟昭英和我到C.I.T。两个学校都不错,一时很难决定。我和王承书到美国后,请教了王的导师,统计物理学家渥沦伯(Uhlenback)教授,他立即说:当然到普林斯顿。于是我决定了去普林斯顿。我想渥沦伯是对的,我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工作是幸运的!
我在普林斯顿工作七年,实验室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他们对科学实验很重视,对科学的发展、对科学工作者非常爱护,我对这一段的工作也很满意。
由选著中看出,在普林斯顿我与同事们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与罗森布鲁姆(S.Rosenblum)合作建造了一台α粒子能谱仪,并利用这套仪器测量了几种放射性元素的α粒子能谱;二是设计建造了一套自动控制、选择和记录宇宙线稀有事例的云室,并利用这套仪器作有关μ子吸收和宇宙线的其它研究工作,如贯穿簇射和V 0粒子的研究。
α粒子能谱仪利用了普林斯顿回旋加速器80厘米直径的磁铁(加速器的其它另件已拆去作国防研究用了),所以能量分辨率相当高。谱仪呈半园形,在通过中心一直线的一端放置α放射源。α放射源以白金为支柱,用窄缝限制α束流的方向,作为“物”空间。在另一端的“象”空间可以形成线状能谱。从窄缝出来的α粒子经过磁铁偏转,不同动量的粒子聚焦成一条一条的线段,用多丝α—火花室或核乳胶片作记录。核乳胶片与a粒子的入射方向有一定的倾斜度,在乳胶片上可以分辨α粒子的径迹是否来自α源。
这α火花室由八根丝组成,只对游离大的α粒子灵敏,对β不灵敏,当α粒子进人时,肉眼可以看见火花。这是最早的火花室探测器。这种探测器的主意是罗森布鲁姆提出的,我不过作了些工作,完成了设计、加工,使它成为现实,特别是在强磁场与真空中可以使用。有的文章谈到这种新型探测器时只提到我,没提到罗森布鲁姆,这是不公道的。
我们知道,α粒子在重物质中散射得很厉害。为了减轻α粒子的散射,谱仪的真空盒要选用尽量轻的物质。当时是用透明的有机玻璃造的,探测器的移动可以从外面看见,特别是多丝室的火花,都可以清楚地看见,非常方便。与计数器比较起来,乳胶片扫描麻烦,但径迹可以永久保存,而且空间分辨率高。
罗森布鲁姆是法国人,比我年长十三岁。他是居里夫人多年的助手,也是长射程α粒子的发现者,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前辈。他比我早一年多到普林斯顿。α谱仪的主体设计和几个部件的加工是他和实验室有经验的工人共同完成的。除了在普林斯顿工作,他还在纽约兼一个工厂的工作。我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只有九个月,他就回巴黎了。我跟他学了很多东西,要是他不回去,工作可以作得更好,我可以向他学得更多。他走后,我在实验室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帮助下完成了谱仪的设计加工和安装调试,使全套仪器运转工作,并初步测量了钋、镭等元素的α谱线。
随着谱仪建造的进展,学校在人员很缺的情况下还给我配了两位助手。一位是研究生,另一位妇女帮助扫描乳胶片。
头一个作的是钋(Polonim)的α能谱。测出的能谱主峰位置和前人的结果完全一样,只是更准确一些。奇怪的是,在低能方向有好几条精细结构,强度约为主峰的万分之一。很难把这些α粒子解释为核内来的。这些α粒子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密执安大学韦迪(Waddy)教授的小组用比较小的α谱仪也观察到了相似的现象。理论家伽莫夫(G.Gamow)对此很感兴趣,我和他讨论过,想出的几个机制都被否定了。看来,它们可能是在核外形成的,或由α粒子在源的白金支柱固体表面作用形成,抑或由于统计涨落。但后者的可能比较小。
这时正是一九四五年,实验室由国防工作转回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要恢复回旋加速器作研究,催了好几次,最后不得不拆掉α谱仪。所以上面所介绍的现象未能深人观察、研究,始终未得到答案,这是我不满意的一个方面。直到现在想到这事心里仍很不安,因为问题没有解决,不知是什么东西。
我是一九四三年秋天到的普林斯顿。当时除我所在的组外,科学研究差不多都停顿了,有经验的教师基本上都出去了。教学还有一点,我有时候代莱德伯上核物理课。到四五一四六年间,一切又开始恢复正常。
这个阶段有一个人找我好几次,说现在有一个单位对α能谱的研究工作很感兴趣。不仅天然放射物可放出α—射线,人工产生的物质也可以放出α粒子,都需要测量它们的能谱。这个工作可以作一辈子,或许还完不了,待遇也很好。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工作,而且可以把当时正在用的一套仪器带去。我知道这个单位与国防有联系,进去就出不来了,以后回国就麻烦了。我回答说,要在普林斯顿可以考虑,其它地方我哪里都不去。以后这人就没有再来了。
另一个工作是自制一套记录宇宙线的云室系统,作μ子被物质吸收的研究。这项研究从一九四六年开始设计建造仪器,一九四八年底、四九年初有了初步结果,发表在“近代物理评论”上。第一个结论是:μ子和原子核没有强作用。当时还不清楚μ子的性质,若μ与核有核作用,就会放出α粒子或质子,这在云室中易于检查出来。我们的实验室没有观察到这种情况。或者说有很少的迹象,但是又不像。第二个结论是:发现当μ停止在薄板上,有低能电子发出,低能电子的方向指向μ停止的地方。不过这种事例不多。到一九五四年再次总结,μ¯核作用照样没有,μ停止并放出低能电子的事例共有十几个。
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为μ介原子。我们的结果传出去,有的单位有钱的,就议论要赶快造μ子工厂来深入研究原子核。实验室的负责人之一惠勒(G.A.Wheeler)对此很支持,此人很有卡文迪什作风,也给了我很多鼓励。哥伦比亚与普林斯顿很近,两家也常来往,我们就鼓励他们造μ子工厂。一九五三年,哥伦比亚的μ子工厂造成了,第一个实验就是检验上面提到的宇宙线的结果,没有几天就告诉我,定性的结果与我的报导完全一样。我们都很高兴。
μ子工厂可以产生大量的慢μ¯,可以用它与核作用产生的辐射来研究核的结构。比如要研究铅核,铅核的电子有一定的轨道,μ¯进来有的取代一个电子停在定态轨道上,就成为μ介原子。这些电子轨道用普通量子力学可以算得很准。由于μ子的质量比电子大200倍,μ子的某一轨道只应为电子相应轨道的200分之一,即μ子比电子离核更近。所以,用μ子作为探针来观察核结构要准确得多。事先假设一种核结构模型,用量子力学可以计算出μ子的轨道和跃迁及辐射的情况,与实验的测量相比较,就可以知道模型的好坏。
μ子在原子核外边可以处于不同的轨道,有很多种跃迁,放出的X光有时能量很相近,要求探测器有很高的能量分辨率。六十年代以前只有碘化钠,能量分辨率太差,影响了这方面的研究。一九六四年发明了半导体探测器,能量分辨率可以提高几倍、几十倍。吴健雄从六四年就开始用半导体探测器研究μ介原子。全世界这样的组共有六个,吴健雄是第一个。他们花了二十年功夫,差不多把所有的核都作了。吴健雄和希尔(Hill)总结了这个领域的工作结果,写了三大卷书,叫做“μ子物理”(Muon Physics),其中首先提到了我们的工作。
我的一个体会是:像这种定量的工作靠宇宙线是不行的,宇宙线作出定性的工作就可以了,就应该停止了。用宇宙线作十年,用加速器一、两分钟就可以了。定量的研究要让加速器作。发现一种新的物理现象只是认识的开始,不是完了。而物理学的发展,定量的研究是很要紧的。
另一个感想是:探测器的分辨率很重要,没有半导体探测器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μ介原子的深入研究。
后来,因为客观的条件,我不得不转到普渡大学(Purdue)I作。在普林斯顿几年,深感他们继承了卡文迪什的不少传统,恐怕还有发扬光大之势。主要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十分重视科学实验而又希望研究工作者和学生都了解一些物理;2.充分认识物理学本身是实验科学;3.各类技术人员齐备,加工设备更多,组织管理更强;4.各级有经验的实验和理论工作者相互配合密切,富有协作精神。最后一点最重要。各级负责人一心一意为发展科学而工作,诚心诚意爱护科学工作者。我作的μ子吸收工作,从制定方案和实验方法,到仪器的设计、加工、建造、安装、初步运转,不过用了一年多一点的功夫,许多工作都是大家作的,我不过总合一下。
我离开时,普林斯顿又将我使用的整套仪器全部送到普渡大学,让我有机会继续进行μ子吸收的工作。选著关于这项工作的后两篇论文(1954年)就是在普渡写的,包括了研究生的博士论文。
我离开普林斯顿以后,还一直和那里的学者保持着联系,他们也一直关心着我的μ子实验。惠勒曾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给我写信邀我去讨论我的工作。
到普渡后又作了两套仪器,以增加事例的统计量。
四、两次回国的对比
一九三八年我从剑桥回国,在四川大学工作了一个短时间后,转到昆明西南联大工作。
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虽是全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但工作条件很差,根本不可能搞科学研究。我和赵忠尧先生想建造一台静电加速器,一有功夫就上街去跑杂货摊,想凑一些另件。跑了两年,除了找敲水壶的工人作了一个铜球,搞到了一点输送带作了个架子外,其它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两年的努力算是徒劳了。我们感叹地说,这项工作只有留给后代去完成了!
由于工作条件不具备,我就改作宇宙线。有三个年轻人帮我的忙,其中一个叫郭一真,一个叫黄永泰。我们什么都从零开始,自己准备吹玻璃的工具,自己吹玻璃作盖革计数管。作出了三根,作了三路符合,后来又扩充到四路符合。当时在昆明大普吉,清华有个无线电研究所,我们在它旁边找了个仓库,测量了宇宙线强度随天项角和方位角的变化,在中国物理学会的年会上作了报告。
接下来的一项工作是与王承书合作,分析当时的核物理数据,分析了β衰变中的禁戒衰变、容许衰变和核能级数据。
除此,我在联大开了核物理课程,这是头一次在国内教核物理。课程的名称是“天然放射性和原子核物理”,对象是助教和研究生。听的人还不少,虞福春、唐敖庆、梅镇岳(他们当时是助教)、杨振宁(当时是研究生)都参加过听课。这门课开了两次,我也从开课中学了不少东西。
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五六年。
解放初,我在美国接到叶企孙、吴有训先生的电报,要我去东德参加中国的代表团,庆祝东德的科学院成立三百周年。当时王承书再有两个月就要生孩子了,我不能抽身前往,只好回电表示歉意。朝鲜战争开始后,回国就困难了。这时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由英国回国。我就给当年剑桥的老师考克饶夫写了信。考克饶夫当时主持英国原子能事业,他建立了哈威尔(Harwell)研究中心,卢瑟福实验室可能也是他主持筹建的。西欧中心的阿达姆斯(J.B.Adams)当时就是他的助手。按照美国的规定,在大学工作七年,就可以休假一年。我给他写信的意思是,希望到他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到了英国后,我再设法回国。
当时在考克饶夫手下工作的人有跑到东德和苏联的,听说美国和英国都对他有意见。我写了信后,也不抱多大希望,估计他可能不理我。不料他很快回了信,叫我到英国去,安排我在牛津大学作宇宙线研究,经费由哈威尔支付。但是,办出境手续遇到了困难。英国领事馆的一名官员坦率地告诉我说:我劝你不要再试了。
考克饶夫倒是宁愿冒险也要帮我的忙。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考克饶夫给我的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希望我九月底之前能到英国。但是我想,如果我到了英国再回来,一定会给他多添不少麻烦。在普渡大学的几年,我的处境比较困难。因为我要求回国,联邦调查局对我很注意。台湾的人经常到这个学校活动。他们一来,要会餐什么的,我就借故走开。有时在外面没事,只好到电影院消磨时光。所幸和我一起工作的几位年轻人对我非常好,经常和我在一起,否则我是很难在那里呆下去的。照片上这几位就是我的学生。其中B.Wallenmeyer现为美国能源部官员。
第二次回国时,已解放六年多了。突然感到人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了。发展科学的气魄、工作的规模都完全不一样了。大学里学生很多,研究所也很大了,与过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回来时,按照当年在昆明的条件,买了一点仪器带回来。回来一看,国内都有,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云大。抗战时,熊庆来先生当云南大学校长,托华罗庚拉我去兼课一年。当时云大条件很差,我在数理系教三年级的光学,学生少得很。这次回来去昆明,云大杨桂宫先生带我参观物理实验室,大不一样了。全校有一千多人学普通物理,实验仪器有很多是由学校工厂生产的,做了很多套,没有三个人、四个人同用一套仪器的。我返回北京去看熊庆来先生,告诉他这些变化。他回忆说:那时在中国做一个学者很难很难啊,什么都得自己来。
回来后看到,国内很重视唯物辩证法的学习,提倡实事求是,提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从前都是不大讲的。我很赞赏毛主席关于“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思想,很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我深深感到,解放以后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底子。
五、教学和科研的体会
最近,美术界举办了“吴作人艺术活动六十周年”展览,吴老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式。我不懂美术,但看到吴老对记者介绍他六十年执教和创作的体会,却深有同感。表面看来,搞美术和搞自然科学差别很大,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的基本规律。
吴先生提倡启发式教学,他不轻易给学生改画,而是指出思路,或带领学生到现场与实物对比、考察、讨论,让学生对客体有一个确实的了解,由学生自己去思考,去创作。到现场看,等于我们作实验,通过科学实验的实践,让学生对自然现象有一个确实的了解,并通过脑子的思维加工,产生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
为了培养出有创造精神的人才,吴先生认为要经常掌握好严与宽、博与专、放与收这三个关系。这三对矛盾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其基本点是启发、调动学生的自觉性,独创性,让学生的“内因起作用”。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也一样。有的要严,基本功、基本概念一定要严,基本关系(如实验和理论的关系)一定要弄清,基本的实验一定要严,要让学生真正弄懂;但有的就不必那么严了,有的知识性、消息性的东西(所谓 informative knowledge),像看报一样,看过就可以了,不必要那么严。博与专的关系,总是要先专后博。一个人不可能一开始就博,否则就没有底了。基本的知识掌握了,就可以在一个方面深入,其它需要的知识再慢慢补进去。我在理论方面的一些知识就是后来慢慢补的,开始不可能有那么多功夫学。放与收的关系,放是需要的,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集思广益,但也不能无休止。就象讨论一个问题,应该放开讨论,但如果争论不休,再讨论两天也不一定有结果,就需要收。
吴作人先生几十年为我国美术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画家和美术工作者,他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是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
结束语
在以上回忆中,我着重强调了科学实验的重要性。我们不要夜郎自大,要承认我们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和一千多年科举制度的影响,要承认我们搞科学实验没有传统,要努力除掉旧的影响。
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十几年前,一次美国费米实验室的莱德曼(L.M.Lederman)教授问我,毛主席接见李政道时谈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据说谈了实验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他立刻说:我不相信会谈这个显而易见(trivial)的问题。所以在西方,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论述,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而在中国,确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无数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是行的。有正确的指导思想,给他一个环境,可以作出好成绩来。党的领导很重要,不然一盘散沙作不了什么。在党的领导下,没有几年就作出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我们中华民族只是一时落后,补救起来必将是很快的。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