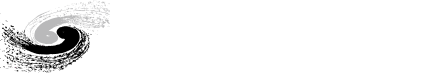我始终总是称他为张教授,即使在我作为科学家功成名就,随后的岁月里我步入花甲之年以后的岁月里,作为科学家功成名就时我依亦然这样称呼他。这一称呼礼节与其说是拘泥于礼仪,倒不如说是对他尊敬的象征。并不是出自于他距我遥远,而是因为,他是世间最友善和最谦虚的人,。与其说是拘泥于礼仪,倒不如说是对他尊敬的象征。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张文裕教授从普林斯顿大学来到普渡大学时,我是三年级的研究生,正参加建造一台300 MeV电子同步加速器。张文裕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期间,在宇宙线受阻μ子的研究中,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他发现的μ子X射线,为我们了解μ子是重电子,可在原子核玻尔轨道中捕获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他想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想继续探索宇宙线相互作用物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宇宙线辐射研究在核相互作用内部秘密的探索中处于领先地位。张教授从未想远离对此研究的关注。对他来说,更深的问题仅是那些值得他献出自己一生的问题。
我们何时曾经相见,已记不准确。但小组变更时,我选择在哪儿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却记忆犹新。张教授的热情完全征服了我的心。
张教授带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和J. 温克勒(Winckler)建造的云室。另外一名叫Gustavo del Castillo的研究生和我,在物理楼一层中等程度大小的实验室里与他一起组装设备。张教授几乎和我们学生一样,总是在实验室里工作,我们生活得非常开心。
我最初参与的云室实验工作没有延续多久,原因是张教授建议我选择利用原子核研究正负电子散射作为我的论文题目。他想让我测量微分截面之差,揭示虚湮灭(巴巴)项效应。这是个基本问题,具有挑战性,但可由研究生解决。这又是一个非常大公无私的抉择,展示张教授人格的范例。他可以提出一个论文题目,进一步提高他自己在云室宇宙线相互作用研究中的兴趣,然而他却提出一个与宇宙线物理完全无关,需要崭新装置以便我获得最广泛经验的题目。他把实验室的一角分给我,集中精力,将15小时用于云室研究上,包括建造第二个云室,测量原来云室中形成的粒子的相互作用。对只有一位教授和几个研究生的小组来说,没有技术支持,有的只是系里的一个小加工车间,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张教授完全置身于新装置的建造,那些只知道他是管理者的人欣赏他在实验上亲自动手的一面。张教授分担了金属的切割与钻孔、衬垫的制作、上润滑油及其装配、布线和测试控制线路,并额外分担了无休止地清洗、举起和上紧螺栓,接着是拆了装装了拆的装配任务,在我的记忆力里,云室连续开了关关了又开,永无休止,旨在解决必然存在的问题。
那些岁月里实验装置的建造、取数据和数据分析,在我的记忆里不多,记忆多的是张教授他本人。他笑容可掬,总是谦恭有礼,生活简朴。他是一个有理论倾向嗜好读书在物理的历史和哲学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人,一位热情无限、充满乐观主义,总给人以鼓舞和忠告,并不断给我提供许多从未记下和再也记不起来的贴切的中国格言的人。他的两句名言成为永恒的指南,现释义于此。我们准备论文时,张教授常说:“写论文时,要总觉得好像你最坏的敌人从你背后伸过头来看你。”这是忠言,即使最坏的敌人是你最好的朋友。他说:“你们必须十分小心地选择研究的问题。请记住:几乎每项实验研究的寿命,不管其内在的价值如何,都需要相当的时间,可能超过5年。在你们现行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多个5年,所以选题前要认真考虑其重要性。”
张教授邀请我到他家坐客时,遇见本人就是著名物理学家的王承书,她向我介绍中国的烹饪,她准备的那顿中餐对我来说仍是佳肴。她几次劝我用另一道新上的美好菜肴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次我还见到了他们幼小的儿子张哲——王承书的骄傲。
我论文完成后,负责指导我工作的张教授为我找到一个博士后的位置,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Maurice Goldhaber手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仅在一年后,张教授便返回中国。虽然我们分别久远,联系甚少,但通过物理传递消息的途径,我们仍保持着联系。在正常通信困难的情况下,他的国际声望当时更为显赫。张教授听说我结了婚,便送我一份精美的结婚礼品。我把我两个儿子的进步情况告诉给他,他把张哲的情况告诉给我。
在普渡大学时,张教授常常谈到北京。他描绘那里的公园、街道和文化。对我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钟爱中国的京剧艺术。他常说,将来有一天,你会访问北京,亲自目睹中国的京剧艺术。1975年,张教授邀请我们全家访问中国。这是一次快乐的大团圆,是我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刻。1977年我妻子和我及1980年我妻子、两个儿子和我再次应邀访华。1980年那次访华,我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了一个月,令人兴奋不已。这些访问加深了新老之间的友好关系。我特别感激的是张哲、他妻子郭旃和他们的儿子张旆已成为我们大家庭的成员。
1990年我回到中国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那时他住在医院,已处于弥留之际。他认出了我,他明显愉快的眼神使我感到不虚此行。现在,他走了,但他的遗产永存。除物理外,他为中国留下相当多的成就,也给他的同事和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影响。就很多方面而言,他都是我的“父亲”。无疑,他是我自己20名博士生的“祖父”,其中有些博士生又成了博士生的“父亲”。在寻找物理真理,要用献身精神,充满快乐和无限乐观主义进行的探索中,我们向他学到了最高的行为标准。
(翻译:侯儒成)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