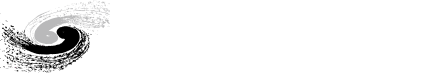中学和大学时期(1916-1925)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初叶。二十世纪是一个斗争激烈、变革迅速的世纪。我自幼身体孱弱,自感不能适应激烈斗争的行列,决心听从先父教训,刻苦学习,打好基础,以备日后作一个有用于社会的人。
我出生时,母亲已46岁。父母亲老年得子,又加我身体弱小,对我管教格外严厉。上小学时,父母不许我上体操课,我的体操成绩因此总是零分。到了中学,也从不让我参加爬山、游泳等活动,我从小只是体育场边的观众。五十多岁时,我才迫切感到锻炼身体的需要,开始学游泳、滑冰,虽然晚了一些,仍然受益非浅。
父亲早年自学医道,行医为生。他看到社会上贫穷落后、贫富不均的现象,常想为国出力,又感知识不足,力不从心。因此,他只望我努力读书,将来为国为民出力。我依照父亲的教导,脑中无非是我国古代先哲名言,再加西方革新思想,可以总结为爱国主义。
十五岁那年进入诸暨县立中学读书。在学校里,我的学习兴趣颇广,文理科并重。记得国文老师常给我额外布置读些古文,使我受益不少,可惜以后未能在这方面进一步深入。但数理化等科目中的科学道理,更能吸引我的求知欲望。
四年后中学毕业,按照父亲的意思和个人的兴趣,我选择报考了完全免费的南京高等师范。1920年秋进入数理化部就读时,南京高师正在扩建为东南大学,数、理、化三系均属于当时的文理科,此外还有农、工、商等科。为了获得较多动手做科学实验的机会,加之当时化学系有孙洪芬、张子高、王季梁等诸位教授,师资力量较强,我选择了文理科的化学系。但在学习中,我一直对数学、物理的课程也同样重视。这倒为我日后担任物理助教,并进而转人物理界打下了基础。
刚进大学时,由于在县立中学英文底子较薄,确实花了一番力气。高师一年级的物理课程选用密立根(R.Millikan)和盖尔(Gale)两教授合编的英文物理课本“First Course in Physics”。一些从市立中学来的同学在中学里就已学过这个课本,而我边查字典边学习,很是吃力。但过了一个多月,我已能适应新环境,不再为英文的物理课本发愁了。由此可见,外语虽是人门必不可少的工具,但起主要作用的归根结底还是对于学科本身的掌握程度。1924年春,我便提前半年修完了高师的学分。当时因父亲去世,家境困难,我决定先就业,同时争取进修机会。东南大学物理系正好缺少助教,学校根据我在校的物理成绩,让我担任了物理系的助教。我一面教书,一面参加听课、考试,并进入暑期学校学习。次年便补足高师与大学本科的学分差额,取得了东南大学毕业资格。
1925年夏,北京清华学堂筹办大学本科,请叶企孙教授前往任教。由于我在东南大学曾担任他的助教,准备物理实验,两人相处很好,他便邀我和施汝为一同前往清华。叶企孙教授为人严肃庄重,教书极为认真,对我的教学、科研都有很深的影响。在清华,我第一年仍担任助教。第二年起任教员,负责实验课。并与其他教师一起,为大学的物理实验室制备仪器。当时国内大学理科的水平与西方相比尚有不少差距。在清华任教期间,得有机会自习。补充大学物理系的必修课程。达到国外较好大学的水平。还和学生们一起读了德文,听了法文。
看到国内水平与国外的差距,我决定争取出国留学。当时,清华的教师每六年有一次公费出国进修一年的机会。但我不想等这么久。靠自筹经费于1927年去美国留学。除过去三年教书的工资结余及师友借助外,尚申请到清华大学的国外生活半费补助金每月40美金。行前,与郑毓英女士成婚。她回到诸暨老家,陪伴我七十多岁的老母,代我尽了孝心。
在美国留学时期(1927-1931年冬)
到美国后,我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部,师从密立根(R.A.Millikan)教授。进行实验物理研究。第一年念基础课程,并顺利通过了预试。由于导师密立根教授根据预试成绩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有力推荐,以后三年,我都申请到每年一千美金的科研补助金。便把原来清华大学的半费补助金转给了别的同学。
密立根教授起初给我一个利用光学干涉仪的论文题目。直接指导这项工作的研究员人很和气,“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的题目,并说:“这个题目你考虑一下。”说是这么说,这次实际上是不容我多考虑的。偏偏我过分老实,觉得测量吸收系数还嫌简单,竟回答说:“好,我考虑一下。”密立根教授一听,当场就发火了,说道:“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相当重要。我们看了你的成绩,觉得你做还比较合适。你要是不做,告诉我就是了,不必再考虑。”我连忙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题目。回想起来,密立根教授为我选择的这个题目,不仅能学到实验技术,物理上也是极有意义的。这一点,我日后才逐渐有深刻体会。
到加州的第二年,我便开始作硬γ射线吸收系数的测量。当时,人们认为g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主要是自由电子的康普顿(A.Compton)散射所引起的。用于计算吸收系数的克莱因-仁科(Klein-Nishim)公式则是当时刚刚问世。密立根教授让我通过实验测量,验证这一公式的正确性。我所用的g射线是ThC“所放出的能量为2.65 MeV的硬γ射线。实验室工作紧张时,我们这些做实验的人常常是上午上课,下午准备仪器,晚上乘夜深人静,通宵取数据。为保证半小时左右取一次数,不得不靠闹钟来提醒自己。
但是,当我将测量的结果与克莱因-仁科公式相比较时,发现硬γ射线只有在轻元素上的散射才符合公式的预言。而当硬γ射线通过重元素,譬如铅时,所测得的吸收系数比公式的结果大了约40%。1929年底,我将结果整理写成论文。但由于实验结果与密立根教授预期的不相符,他不甚相信。文章交给他之后两三个月仍无回音,我心中甚为焦急。幸而替密立根教授代管研究生工作的鲍文(I.S.Bowen)教授十分了解该实验从仪器设计到结果分析的全过程,他向密立根教授保证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文章才得以于1930年5月在美国的《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发表。当我在加州作硬γ射线吸收系数测量时,英、德两国有几位物理学家也在进行这一测量。三处同时分别发现了硬γ射线在重元素上的这种反常吸收,并都认为可能是原子核的作用所引起的。
吸收系数的测量结束后,我想进一步研究硬γ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机制,打算设计一个新的实验,观测重元素对硬γ射线的散射现象。与鲍文教授商量时,他说:“测量吸收系数,作为你的学位论文已经够了,结果也已经有了。不过,如果你要进一步研究,当然很好。”当时虽然离毕业只有大半年时间了,但由于有了第一个实验的经验,我还是决心一试。我于1930年春天开始用高气压电离室和真空静电计进行测量。没想到,一开始就遇到了问题:那时,德国的豪夫曼(Hoffmann)教授发明了一种真空静电计。加州理工学院的工厂仿制了一批。这种静电计中有一根极细的白金丝,是用包银的白金丝拉制后,再将外面的银用酸腐蚀掉制成的。白金丝的上端通过一个焊接点和电离室的中心电极相连,下端连接指针。可是,接通电源后静电计的指针甚至十几分钟后还达不到稳定点。密立根教授对我和另外两个使用这种静电计的学生说:“这种新产品我也没有用过,你们应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起初,大家都以为是环境的振动引起指针的不稳定,想了各种办法防止振动,甚至把静电计的支架用弹簧挂住,放在四个网球支撑的平板上,但都是枉然。后来我想到,指针达不到稳定值,可能是因为导电不良。于是我在焊接处滴了一些导电的碳制黑墨水,指针立即变得很灵活,总算解决了这一难题,并开始测量电离电流。由于反常吸收只在重元素上被观测到,我决定选择Al与Pb为轻、重元素的代表,比较在这两种元素上的散射强度。这个实验一直忙到当年九月才算结束,准备好久的暑期旅行因此取消。可测得的结果如此有趣,足以补偿放弃休息的损失。
我的这个实验结果首次发现,伴随着硬γ射线在重元素中的反常吸收,还存在一种特殊辐射。由于电离电流很弱,要将特殊辐射与本底分开是很困难的。康普顿散射主要在朝前方向,朝后的部分不仅强度弱,并且能量也低,因而在朝后方向观测到的特殊辐射信号最清楚。我不仅测得了这种特殊辐射的能量大约等于一个电子的质量,而且还测出它的角分布大致为各向同性。我将这一结果写成第二篇论文《硬γ射线的散射》,于1930年10月发表于美国的《物理评论》杂志。
说来有趣,一直到我的论文结束时,密立根教授还记得我挑论文题目的事。在评议论文时,还在教授们面前讲我的笑话,说:“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我那时给他这个题目,他还说要考虑考虑。”惹得同事们善意地哈哈大笑。不过,他们对我的论文是满意的。后来,密立根教授在他1946年出版的专著《电子、质子、光子、中子、介子和宇宙线》中还多处引述了我论文中的结果。
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揭示了一种新的相互作用机制。但是,当时还不能认识到这些现象的具体机理。与我同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还有安德逊(C.D.Anderson),他对这些结果很感兴趣。我们也曾谈起,应当在云室中做一做这个实验,可惜后来这个想法未能实现。直到1932年,安德逊在宇宙线的云雾室照片中发现了正电子径迹,人们才逐步认识到:三个实验组同时发现的反常吸收是由于部分硬γ射线经过原子核附近时转化为正负电子对;而我首先发现的特殊辐射则是一对正负电子湮灭并转化为一对光子的湮灭辐射。
关于人们对我这部分工作的评价,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比较起来,我所作的第二个实验的难度比第一个大。因为散射的强度很弱,测量时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细心。由于我选用了高压电离室和真空静电计进行测量,本底比较少,涨落也小,因而结果比较稳定和干净;但是在我的论文发表后的一两年内,其他人重复这一实验时,用盖革计数器进行测量,也没有用高压电离室,本底与涨落都比较大,得到相互矛盾与不确定的结果。这些矛盾,一度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至于论文本身,可惜写得太简短,与它所包含的内容不甚相称;加上勃莱克特(P.Blackett)与奥恰里尼(G.0cchidini)在他们的论述《电子对湮灭》的著名论文中引述我的工作时,发生了不应有的错误。由于这种种历史的原因,我的这些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最近从1983年起,杨振宁教授花了不少精力,收集整理资料,写成文章发表,帮助澄清了这段历史,并且同意将他的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这本文集。我十分感激杨先生为此所作的这许多努力。
在美国的这段生活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从小身体瘦弱,缺少锻炼,所以体力不足,双手操作不灵。自己感到,无论为科学实验的需要,或为健康的需要,都必须加强体力活动。适值在美国市场上,见到破旧汽车非常便宜,即以25美元的代价购得一辆破旧汽车,在课余时间学习简单的汽车修理和驾驶。对于一辆破旧的汽车,自然说不上需要和消遣。凡休息日,我常常满身油污,仰卧于汽车下面,拆拆装装。我在修理汽车的过程中,不但锻炼了动手能力,还有在辛苦以后获得的欣慰。另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因此得到一个乐于助人的朋友豪义特(A.Hoyt)。我们从谈汽车开始,谈到风俗人情、科学研究。说这是我在美国除了关于论文所受的指导以外最大的收获,一点也不夸大。可惜在我回国之后不久,他因病去世。这是我莫大的遗憾。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1932-1945)
九· 一八事变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并吞整个中国的野心。当时我尚在国外,国难当头,心中焦虑,决心尽速回国。个人原打算专心于教学与科研,为国家做点贡献。可面对凶狂的敌人,科学救国、工业救国都不能应急,只能先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教学和科研上,并尽一切可能探索为国效劳的道路。
当时,清华大学正在成长过程中,师生全都非常积极。叶企孙教授从理学院调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由吴有训教授接任理学院院长,我曾一度接任物理系主任。系里还有萨本栋、周培源等多位教授。这个时期,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为努力办好物理系,大家齐心协力,进行教学和科研,实为难得。科研方面,各人结合自己专业开展研究,气氛很好。我在德国时,还联系聘请了一位技工来清华,协助制作象小型云雾室等科研设备。我们自己动手制作盖革计数器之类的简单设备,还与协和医院联系,将他们用过的氡管借来作为实验用的放射源。我们先后在g射线、人工放射性、中子共振等课题上做了一些工作。之后,由于日寇的步步进逼,大部分国土沦陷,清华大学南迁,研究工作不得已而中断。
除科研教学外,我日夜苦思焦虑,想找出一条立即可以生效的救国道路。我曾尝试了多种途径: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工业救国等等。但由于个人出身及身体等条件的限制,所选择的多为改良的道路,始终未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与付出的努力相比,收效甚微。尽管碰了不少钉子,但毕竟身体力行,尽了努力,从各个方向试着去做一点于国家民族和老百姓有益的事。
那时有位搞社会教育的晏阳初先生,对平民教育很热心,在河北定县农村搞了一个平民教育的实验点。我利用暑假去定县参观,既了解到中国农村的贫穷困苦,又看到那里缺少文化,急待改造。虽然这种投入很局限,但对我触动很大。对我以后参加办铅笔厂,替国家采购仪器、部件,加工设计等都是有影响的。我去做这些事。都是经过考虑的,都是克服了困难,尽力去办好的。不久,华北沦陷,平民教育的路也没有了。
抱着工业救国的良好愿望,我又想结合出国数年积累的经验,在国内仅有的少数企业中寻觅伙伴,探索技术,创办小型的国产工业。经过反复酝酿,我联合叶企孙教授和施汝为、张大煜等少数友人,拿出自己的工资积余,决定集资创办一个小小的铅笔厂。建铅笔厂所需技术与投资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大家不以营利为目的,小则可以发展实用科学,大则创办国产工业,以此作为从事实际生产,为国出力的起点。我们力求在国内完成整个生产过程。除从国外购进必要的机器设备外。我还与郭子明等几位技工进行削木头、制铅芯等必须的工艺实验,先后经历了不少困难。由于当时国难当头,大家义愤填膺,这个厂得以在困难中办起来,全由大家的爱国热情所支持。厂址原定在北京,后由于日寇步步进逼,只得改建在上海。厂名定为“长城铅笔厂”,“长城牌”铅笔由此问世。由于资金薄弱,缺乏管理经验,加上政局动荡,我们又远在北京或西南内地,对于具体管理鞭长莫及,真是难上加难。工厂几经盛衰起落,能渡过抗战,一直坚持到胜利,实在不容易。解放后,这个厂改建成“中国铅笔厂”,五十年代,“长城牌”铅笔改名为“中华牌”,工厂也得到很大发展。这样,三十年代开始生产的“长城牌”铅笔总算没有中途夭折。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京无法安身,我们全家便辗转南下到昆明。第二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共同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大,我便在那里任教,前后呆了八年之久。这期间,除了教学之外。我还与张文裕教授用盖革-密勒计数器作了一些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作。可是,随着战局紧张,生活变得很不安定。由于物价飞涨,教授们不得不想办法挣钱贴补家用。我想办法自制些肥皂出售,方能勉强维持。加上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早上骑着自行车去上课,课程进行中,警报一响,大家立即把书夹在自行车后,骑车去找防空洞。家人则更是扶老携幼逃往城外。开始人们以为安全的城墙根很快被炸为废墟。华罗庚先生甚至被爆炸的土块埋住后逃生。尽管如此,西南联大聚集了各地的许多人才,教学工作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一直坚持进行,也的确培养出不少新生力量。
1945年冬,我应中央大学吴有训校长邀请,离开西南联大,赴重庆担任了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
第二次去美国时期(1946-1950)
l946年夏,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验。国民党政府派两个代表前去参观。我受中央研究院的推荐,作为科学家的代表。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筹了五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而且,核物理在那时是一门新兴的基础学科,国家总是需要它的。所以我就答应在指定的财力范围以内,以最经济的办法,购买一些对于学习原子核物理最有用的器材。就当时情况,经济的限制是压倒一切的。全部的财力是准备用于购买核物理器材的五万美金和以后托管购买其他学科器材的经费七万美金。个人的生活费实报实销,谈不上薪给。由于经费紧张,我在吃住方面尽量节省,每年开支两千美金。这是很难与当时公派出国人员每年一万美金的生活水平相比的。此外,在个人控制下的还有回国的航空旅费和头三个月出差费的余数而已。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加速器。而当时订购一台完整的200万电子伏的静电加速器要40万美金以上。很明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购买任何完整的设备。经与友人多次商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购买国内难于买到的部件和其他少量的核物理器材。当然,这是条极为费力费时的路。
照这个计划,我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学习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和加速管的制造。该实验室主任屈润普(Trump)热心而又和气,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为我想了好多办法。他让我利用他们的资料,还介绍给我另一位专家,帮我解决问题;又将实验室里准备拆去的一台旧的大气型静电加速器转给我作试验用。后来l986年我国原子能研究院从美国购买的串列式静电加速器就是屈润普教授他们的公司供应的。在麻省理工学院加速器实验室呆了半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学习离子源的技术,我转去华盛顿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半年。那里有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工作,学习的环境也很好。当时,毕德显先生正准备回国,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电子学及其他零星器材。毕德显先生为人极为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半年以后。为了寻觅厂家定制加速器部件,我又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线研究室。因为我对宇宙线研究有兴趣,该研究室主任罗西(B.Rossi)人又很和气,欢迎我在他那里工作。罗西教授是意大利人,他很了解我的工作。1952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高能粒子》中就引用了不少我拍的云雾室照片。我当时联系定做加速器的各种部件,需要打听情况,麻省理工学院附近有好多朋友可以帮忙。由于这些难得的有利因素,我就决定暂时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直到结束采购器材的任务。加速器上的机械设备,都是特种型号,每种用量不大,加工精度要求又高,好的工厂很忙,不愿接受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小交易。我为此奔走多日,有时一天要跑十几处地方,最后联系到一个开价较为合理的制造飞机零件的加工厂。这样,加速器运转部分,绝缘柱及电极的制造总算有了着落。与此同时。还替中央大学定制了一个多板云雾室,并且买好了与此配套的照相设备。加上核物理实验及电子学器材,都是用手头那点钱购置的。这段期间,我曾在几个加速器、宇宙线实验室义务工作。以换取学习与咨询的方便。我的义务劳动也换得了一批代制的电子学仪器和其他零星器材,节约了购置设备的开支。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作前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
1948年冬季,我结束了前中央研究院所委托的购买简单的核物理实验设备的任务,原来预计即可回国。但那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局的变化很大,感到不如待局势平息之后,回国参加和平建设。再则,那时核物理是战争中崛起的学科,个人对于加速器上的实验亦没有经验,因此决定在美国再留些时间,多学些必要的实验技术,以备随时回国。我在十余年前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学位,有不少师友、因此与他们相商,在加州理工学院短期从事研究工作。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有两台中等大小的静电加速器,具备研究核反应所需要的重粒子和β谱仪,正适合于我们初学的借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开洛辐射实验室工作了近两年。
我第二次去美国期间。为了联系定制器材,曾先后访问了几个科学实验室,在那里短期做静电加速器实验,利用云雾室做了宇宙线实验。在这个过程中,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学术上的友谊。可惜以后由于中美长期断交,一直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将主要精力用于定制设备的同时,我也抓紧时间在宇宙线及质子、α核反应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终因精力有限,收敛不大。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如今我回首往事,固然仍为那几年失去了搞科研的宝贵机会而惋惜,但更为自己的确把精力用在了对祖国科学发展有益的事情上而自慰!
1949年,我开始作回国的准备工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自然是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与核物理实验器材。不巧的是,我起先联系的是一个国民党官僚资本经营的轮船公司,货已经存到了他们联系的仓库里。为了将器材运回新中国,必须设法转到别的运输公司。我利用1949-1950年初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设法将货取出来,重新联系了一个轮船公司,办理托运回新中国的手续。没想到,联邦调查局盯上了这批仪器设备。他们不但派人私自到运输公司开箱检查,还到加州理工学院去调查。幸好,加州理工学院回答问题的杜曼(Dumand)教授为人正直,告诉他们这些器材与原子武器毫无关系。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扣去了部分器材。我特别感到可惜的是,他们扣下了四套完整的供核物理实验用的电子学线路。不仅因为这些线路正是我们所急需,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线路是麻省理工学院宇宙线实验室罗西主任专门派人为我们焊接制造的。后来实在检查不出什么问题,联邦调查局又把这些扣下的器材运回了加州理工学院。中美间恢复通信后,美国的同行科学家们还来信表示,器材由他们暂时代为保管,中美建交后就寄来给我。回想定制器材的前前后后,若没有这些国外同行的帮助和支援,这件事是很难办成的。我对联邦调查局私自开箱检查一事极为恼火,偏偏运输公司还找上门来,要我交重新包装的手续费。我当时就发火了:“谁叫你们打开的你们向谁收!我的东西你们随便给人看就不对!”运输公司的人回答说:“那是什么机关,能不让看吗?”是啊,这种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想想只要器材能运回来,再付一次费用也只好算了。这样,我在美国定制的这批器材装了大小三十多箱,总算装船起运了。
1950年春天,我也准备返回祖国。但是,这时中美之间的通航却已中止了,我不得不想别的办法。取道香港很难得到英国签证,绕道欧洲又颇费时日。这时,一家轮船公司愿意帮忙办理香港的过境签证。经过五个月的等待,我与一批急于回国的留美人员终于得到了香港的过境签证,于八月底在洛杉矶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威尔逊总统号”海轮。可一上船,联邦调查局的人又来找麻烦,把我的行李翻了一遍,偏偏扣留了我最宝贵的东西:一批公开出版的物理书籍和期刊,硬说这些是“不需要的东西”。轮船终于开动了。我尽管可惜那些书籍,倒还庆幸自己得以脱身。
没想到,旅途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船到日本横滨,我和另外两个从加州理工学院回来的人又被美军便衣人员叫去检查,硬说我们可能带有秘密资料,随身行李一件件查,连块肥皂也不放过,称之为“看起来象肥皂的一块东西”,扣下待查。可惜我的工作笔记本都被抄走了。大件行李压在货舱里拿不出来,还要等空船从香港返回时再查。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被关进了日本的巢鸭监狱。无论我们怎样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只是:“我们执行华盛顿的决定。没有权力处理你们的事。”同时,台湾当局则派各种代表威胁劝诱,说只要愿意回美国或去台湾,一切都好商量。如此纠缠了两个月之久。我那时回国的决心已定,反正除了中国大陆我哪儿也不去,一一回绝了这些纠缠。只是不知事情还要拖多久,便决定利用在监狱里的空闲,找到一位同住的懂日文的中国难友当老师,上起了日文课。直到这一年十一月中,在祖国人民和国际科学界同行的声援下,我们才获得释放,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
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时期(1950年11月至今)
经历数月的磨难,我终于在1950年11月底回到解放了的新中国。回国时,感到祖国一切都是新的,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自己向来未曾经过大的场面,又惭愧没有为人民做过多少事,心情很是兴奋与不安,只想尽快投入到具体工作中去,为新中国的科学发展出力。
1951年,我开始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由于我感到自己更愿意也更适合做具体的工作,便决定留在了实验室,着手核物理实验方面的建设。
1953年,近代物理所从城里搬到中关村。那时中关村刚开始建设,一共只有一两座办公楼,仅有的几幢住宅周围都是耕地。当时国内物资非常缺乏,工作甚难开展。为了争取时间,培养干部,大家决心先就力所能及的范围,建立一个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的实验基地,边干边学,逐步掌握理论和技术。到1954年初步建立了中关村的近代物理所工作基地。
我在美国费尽辛苦购置的一点器材,大部分都安全运回了国内。1955年装配完成的我国第一台700 keV质子静电加速器,主要就利用了这些带回来的部件和器材。同时,我们还着手研制一台2.5MeV的高气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这段时期,虽然有时参加些国内外的社会活动,未能始终在实验室与大家共同工作,但回想起来,仍庆幸自己及时回到祖国,参加了新中国最早的加速器的建造及核物理实验室的建立。
那时,研究所里调集了一批业务基础好,又刻苦肯干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国家还从原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等处调来了一批有经验的工人师傅,真是人才济济,朝气蓬勃。加速管的封接是建造加速器的关键步骤之一。我在美国期间,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了这种技术。回国后,与大家一起边干边摸索经验;从磨玻璃环开始,到涂胶、加热封接,每一步都精益求精。这台2.5MeV高气压型的质子静电加速器终于在1958年建成。由于加速管和真空部件做得好,所封接的加速管这么多年没有坏,一直用到现在,质量比苏联进口的还要好。这在当时国内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既无资料可查,又不能出国考察,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建立实验室和研制加速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学习了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离子源技术、核物理实验方法,而且在工作中培养了踏实严谨、一丝不苟的科研态度,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迅速成长起来。虽然现在这两台加速器几乎到了进博物馆的年龄,但在建国初期,它们的确起过示范作用。不少人形容中关村分部是下蛋的老母鸡,这话也许并不为过。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向苏联订购一座原子反应堆,两台回旋加速器和若干测试仪器,并派遣一批中年骨干和青年学生前去学习。1956年在北京远郊坨里兴建的一堆一器与中关村的基地合并成为原子能研究所;中关村部分称为原子能所一部,坨里部分为二部。中关村分部除于1958年建成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外,还着手研制电子直线加速器和进行其他探索性的工作。二部的回旋加速器建成后,我一度参加在回旋加速器上进行的质子弹性散射、氘核削裂反应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另一方面,为了迅速扩大科研队伍,并提高队伍的素质,中国科学院于1958年建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兼任科大近代物理系的主任。由于有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支持,科大的师资和设备都是第一流的,这是最优越的条件。记得那时,我的确花力气请了所内外不少第一流的专家来系里任教,学生的反映也很好。由于与研究所的联系密切,使近代物理系得以较快地建立起一个专业实验室,开设了β谱仪、气泡室、γ共振散射、穆斯堡尔效应、核反应等较先进的实验。我们很注意培养方法,尽可能使学生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得到发展。为了防止实验队伍中缺少理论人才,我们努力使理论、实验专业均衡发展。我们的努力得到了相当的收获,培养出一批理论实验并重的人才。科大能在短短的时间内与国内一流大学获同等声誉,广大师生员工为此作出了艰巨的努力,回想起来绝非易事。
五六十年代,我感到要开展国内的核物理研究工作,至少应对国外的发展情况有所了解,因此我很注意阅读国外书刊,在调研工作上化了不少时间,以了解学科发展动态。同时,我也经常考虑,如何从我国的经济实力出发,尽快发展国内的科研、教育事业,如何促进国内新型低能加速器的建立。为此也作了不少调研和努力。在这期间先后曾就建造串列式加速器、中能加速器、建立中心实验室、缩短学制、成立研究生部等许多与我国科学发展有关的问题向各级领导提出建议。可惜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未能及时得到实现。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天真地将自己对搞好科研工作的一些看法写成大字报。没想到自己不久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因“特嫌”而被隔离审查,文化大革命使我失去了精力、时间、给我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被隔离审查期间,我对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新进行了回顾与思考。我想,一个人能作出多少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决定的。由于我才能微薄,加上条件的限制,工作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为祖国兢兢业业地工作,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没有谋取私利,没有虚度光阴。
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高能加速器的建造终于提到了议事日程。我尽管年龄大了,精力也不济了,但仍坚持尽量多参加些与高能所的建设有关的学术讨论、工作与会议。看着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从破土动工、建成出束到积累数据,看到一批中青年科技人员成长起来。队伍不断壮大,真是感慨万千!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