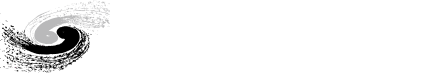中微子,轻盈、诡异、难以捕捉。
它以近似光速运动,不与周围物质发生相互作用,却又是破译宇宙起源与演化密码的钥匙。
如果说探测这种“幽灵”的特性需要运气,那么为之付出17年努力的王贻芳则“碰巧”被“上帝”垂青。
王贻芳说,研究物理学这样一个极少人为干扰的学科是幸福的,而研究中微子,已然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2005年,中国香港。
经过5个小时的拉锯战,谈判桌上的双方早已一脸疲惫。
说是双方,但在人数的对比上颇为悬殊:一端是十余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咄咄逼人;而坐在另一端的代表王贻芳,则有种“单刀赴会”的意味。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大亚湾实验采用谁的方案。当时王贻芳的两难处境是:按照美国的方案走,可以争取到国际合作,项目立项就没有问题,但中方的贡献和地位就有限了;反之,可能就没有国际合作,项目可能根本无法在国内立项,大家过去几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你们的方案存在问题,我不能答应。”王贻芳的内心已经作好了选择。
这场谈判最终不欢而散,双方“连手都没有握”就各自离去,精心准备的晚宴也随即取消。美方的不少专家,还曾是王贻芳的朋友。
这就是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初期的真实写照,相较于2012年3月那段举世闻名的发现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的宣告,王贻芳和他的中微子项目所经历的过往却鲜为人知。
走近“幽灵”的世界
中微子,轻盈、诡异、难以捕捉。
对普通人来说,或许只能从科幻电影《2012》里所谓的“灾难起源”这样的描述中,捕捉到关于中微子的片面印象。但对于中微子真正的特性而言,这仅仅是井底之蛙式的解读。
它以近似光速运动,悄无声息地自由穿行于地球;它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中微子;它是构成物质世界的12种基本粒子中人类了解最少的一个,却又是破译宇宙起源与演化密码最重要的钥匙。
1996年,中微子研究正式进入王贻芳的物理世界。这一年,他加入了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20多人的实验组。除了能参与实验的最初设计和研究方法的讨论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正在进行一个中微子的实验项目。当时,中微子并非研究热门,王贻芳却已沉迷于它的无穷魅力。
如果说成功探测中微子这种“幽灵”的特性需要运气,那么为之付出17年努力的王贻芳则“碰巧”被“上帝”垂青。
2002年12月6日下午5时,王贻芳与日本、美国同行同时宣布,他们发现了核反应堆中产生的中微子消失的现象,这意味着反应堆中产生的中微子发生了振荡,变成了另一种没有被探测到的中微子。
这是国际上首次用人工中微子源证实太阳中微子振荡现象,同时也首次定量给出了太阳中微子振荡参数的唯一解,验证了标准太阳模型是正确的,得出了中微子质量不为零的肯定结论。此外,这个实验也首次探测到了地球本身发出的地质中微子。
“成果不能让给美国”
尽管在美国的实验非常成功,但这距离王贻芳梦想中的中微子研究尚有距离: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中微子研究?
2001年,“和太太僵持了一年”、终于获得“许可”的王贻芳回到中国,开始着力推动和组织我国自己的中微子研究项目。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把方案让给美国,让他们得到成果,这种事情我绝对不能做!”王贻芳告诉《中国科学报》。
所幸,在谈判桌外,王贻芳依靠此前在业内积聚的影响力,聚拢了一批国内和美国华裔科学家的力量,其中包括从美国归来的项目副经理曹俊、项目电子学负责人李小男等一批优秀科学家。
同时,不愿缺席这一将对高能物理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型实验的美国,也组建了新的团队加入到大亚湾实验中。
最终,项目组纳入了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美国、俄罗斯、捷克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研究单位的190多位研究人员,俨然一个“小联合国”。但是,以王贻芳为代表的中方紧紧把握住了实验的主导权。
“一个组单干是很难出成绩的,在国际上一个项目由多个组来做也是常态。”王贻芳说,倘若没有国际合作,这个项目很难做起来。
非常时期的非常项目
走出人才困境后,王贻芳还得解决一个难题:寻找项目资金。
2004年,王贻芳向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项目方案。“科学院觉得项目太小,无法列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计划,但单靠科技部、中科院、自然基金委三家的资金又支持不了”。
后来他又找到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尽管一开始遇到很多困难,但在中科院的斡旋之下,6家单位最终认可了王贻芳的方案,并共同出资1.6亿元,这在我国开创了国家、地方与企业共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先河。
“应该说,这是一件在非常特殊的时期做的非常特殊的项目,各方能够如此团结,是非常不容易的。”王贻芳回忆,这种合作在这6家单位内部都是空前的。
而2003年也注定是不平凡的“中微子之年”,为了测量最后一个未知的中微子混合参数,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7个国家相继提出了8个实验方案。
尽管最终只有中国、法国和韩国的3个方案付诸实践,但国际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在2012年3月王贻芳宣布了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之后仅仅3个星期,韩国的一个实验组就宣布了同样的结果。
这个韩国小组还不无忧郁地在宣布结果论文的引言中说:“我们在准备这篇论文期间,他们(中国方面)就宣布了这项结果。”
实际上,王贻芳小组的领先并非如韩国人想象那般是“抢”出来的。自1999年起,王贻芳就开始琢磨在中国进行中微子研究。4年后,他根据大亚湾的特点,提出了原创性的实验方案和探测器设计,并带领大家进行了前期预研。
与其他方案相比,大亚湾实验方案精度最高,因此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支持。美国方面甚至放弃了本国科学家提出的方案,转而支持王贻芳的项目组,并投入了相当于8000万元人民币的研究设备。
师承丁肇中
从宣布发现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至今,王贻芳已走过了一段科研与管理相结合的物理学之路。走近这位物理学家,人们或许会惊诧于他是如何很好地将两种思维相结合的。
2011年10月,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完成所长换届,王贻芳被任命为所长。在此之前的两个月,他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工程正式开机“捕捉”中微子。
这些正与他的授业恩师丁肇中有关。“我从丁先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条,他让我看到了应该如何组织和协调大型科学实验。”
大学毕业时,王贻芳的老师推荐他报考丁肇中面向全国招收的高能物理研究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能物理在中国属于“冷门中的冷门”,即使有机会出国深造,愿意在这个领域深入的学者也属凤毛麟角,王贻芳就是其中之一。
通过笔试进入面试,王贻芳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影响他一生的导师丁肇中教授:“他年过五旬,红光满面,看起来特别年轻,气质与众不同。他不是一个常人。”
从1985年到1996年,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到瑞士日内瓦,王贻芳在丁肇中的指导下度过了从研究生到博士后的11年。
在丁肇中的L3实验组,王贻芳创造了多项保持至今的纪录:一年时间内发表了3篇论文;1990年出任“新粒子寻找组”组长,在所有L3实验物理分析小组组长中,唯有他是一名学生;1991年,在被L3实验组内部认为是不可能的情况下,精确测量出了陶轻子的极化。
时隔数十年,当年被丁肇中选去参加L3实验的几十位研究生中,至今依旧在高能物理领域的还剩下3人,绝大多数已经“上岸”从商,而回到国内的仅有王贻芳一人。
“幸福而可靠”
如今的王贻芳,已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探测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项目的成功,也给他带来诸多荣誉——2012年“十佳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网“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但他却极为低调,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个人荣誉似乎并不是王贻芳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而此次采访中,王贻芳用了一个很少拿来描述物理学的词汇来形容自己的科研心路——“幸福”。
“对物理学的研究,人为的干扰因素较少,因此它的结论是幸福而可靠的。”这也是王贻芳所倡导的物理学家的品质:不带有任何偏见地保持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和追求。
认识他的人常说:“很少看到有人像他一样,为了物理的真理,如此不近人情。”这或许正是王贻芳的某种“偏执”——不允许任何人用个人色彩来看待物理学实验。
在他眼中,物理学是“极特殊”的,理论和实验结合得非常紧密,他认为“物理学比其他科学更加科学”。
回国十余年,王贻芳发现,与国外科研机构不同的是,国内有些科研机构只是把科学当做“谋生的饭碗”,缺少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精神并未深入人心。
2011年5月3日,王贻芳在本报头版发表了《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几点看法》,结合自己对国外科研机构的了解,王贻芳希望中国科学界应该避免急功近利的思维,努力将目光放到基础科学研究上来。这在当时曾引起不小的反响。
如此急功近利的风气也反映在社会上,中微子的项目成果发布后,不少媒体直接将其同诺贝尔奖联系在一起,理由是此前发现大气中微子振荡、太阳中微子振荡的美国和日本科学家都获得了这一殊荣。
“但大亚湾实验室的这个发现,还只是漫长实验中的一步。”正如中科院院士陈和生在一次采访中表述的那样,尽管国家和社会对诺奖的期待很高,但王贻芳的中微子之路可能还很长。
2013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二期项目即将启动,相比此前,二期项目获得资金和支持要容易得多。而研究中微子似乎已然成为王贻芳的一种生活方式,尽管其应用在几十年之内很可能都不会实现。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3-02-08 第5版 人物周刊)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