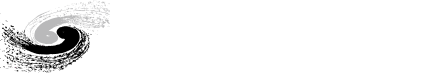戴自海(Henry Tye),1947年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是著名的宇宙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暴涨宇宙论的创始人之一,香港科技大学赛马会高等研究院院长,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
有关杨振宁教授对高能物理(即基础粒子物理,或简称为粒子物理)发展的意见——几点背景和回应。
我个人支持在中国兴建巨型粒子对撞机,而丘成桐教授与王贻芳教授亦已清晰地解释了背后原因。下文将提供这场由1970年开始的讨论的背景资料,或可为这场辩论做出补充。
虽然巨型粒子对撞机在中国兴建与否,最终决定权在于中国决策者,但我认为公众就此议题有开放讨论的机会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现象。通过公开讨论,公众将更了解兴建巨型粒子对撞机的计划,甚至整个中国二十一世纪科研发展的蓝图,从而明白中国在寰宇间的定位。作为一个粒子物理学者,我对对撞机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亦明白在我的有生之年将无法看见巨型对撞机对科研所带来的累累硕果。
杨振宁教授是物理学历史上的巨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贡献是基础粒子物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他已经离开了粒子物理主要研究方向,所以并不容易找到他对于这方面的看法。根据各种直接与间接的来源,他在与黄克孙教授采访时表达的观点被认为是真实的。所以我想在这里引用它。我也将补充一些背景注释。
以下节录自黄克孙教授与杨振宁教授的在2000年的访谈[1],其中谈到1980年发生的事,而当中杨教授就高能物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可以看到他至少直至2000年一直持有这样的看法。黄教授是麻省理工的物理学教授,专门研究统计力学、量子场论以及高能物理。他与杨教授合写了好些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我刚知道我尊敬的老师和朋友黄教授在2016年9月1日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就杨振宁学术资料馆访问杨振宁教授(by黄克孙)
黄:今天是2000年7月29日,我(黄克孙)在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教授的办公室访问他有关统计力学的课题......(前讨论有关统计力学的课题)......
杨:......实情是,基础粒子物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者是过去50年内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它在物理学界鸿霸一方的情况将要来到尽头。
杨: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你好像不在现场。大概在1980年,罗伯特·马沙克教授因为周光召教授的到访(他个人是相当欣赏周光召的),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会议,有许多人参加。会议的最后一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们就高能物理的未来进行了一场小组讨论会。你有听过这故事吗?
黄:没有。
杨:在这日之前,我获邀成为小组讨论员之一,但我拒绝了。我说我没有许多话要说,于是便坐在观众席之上,聆听他们的讨论。那时候的小组讨论员有十位,有马沙克教授、李政道教授、马丁·佩尔教授、Feza Gursey教授、史蒂文·温伯格教授、谢尔登·格拉肖教授,南部阳一郎教授,还有几位来自欧洲的学者,好像周光召教授也在其中。当时的讨论分为两派阵营,一边说W和Z玻色子终有一天会被发现,而另一边则认为不会,但大部份倾向不被发现比较好。你现在可能想知道之后发生了甚么事情。
他们谈论了近一个小时,至讨论将要完结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我的存在,并说:「杨振宁教授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想听听他的意见。」我拒绝了,但他们坚持要我说些什么。当刻,我跟马沙克教授说:「我可以说点什么,但我要先得保证我所说的不会被公开。」他答应了(以后他亦信守诺言)。
于是我说:「在未来的十年(讨论会的主题好像是『高能物理的未来』),我估计高能物理界上最大的发现就是:『高能物理要完了』。」顷刻全场一片寂静,没有人说出一句话,而马沙克教授随即宣布休会。我记得立时几位年轻人一拥而至,尤其是戴自海。你知道谁是戴自海吗?
黄:我知道。
杨:他走过来要与我争论,但我说:「我不会跟你争论的,但请记得,我所说的更多是关于你的未来,而不是我的。」(笑)
黄:这倒是真的,但很多人仍然相信高能物理还有未来。
(采访回到统计物理)......
背景:那1980年的会议是一场小于100人参加的小型学术会议,在当时的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即现今的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又称弗吉尼亚理工)举行。而马沙克教授当时是一位备受敬重的老前辈。
参加小组讨论会中,史蒂文·温伯格教授和谢尔登·格拉肖教授两位则刚在一年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79)。随后马丁·佩尔教授(1995)和南部阳一郎教授(2008)也相继获诺贝尔物理学奖。Feza Gursey是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教授,最后大家知道的李政道教授和周光召教授则不用我多介绍。
对于杨教授的话我不能同意。他认为研究高能物理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他建议当时的年轻学人(包括我)应该转向其他研究项目,而他自己也真实地从1970年代开始从事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事实上当时某些年轻学人听从了他的劝告,从事其他方面的研究并有辉煌的成果)。
到目前为止,历史告诉我们,杨教授对高能物理未来的预测是不正确的。在1980年,W及Z玻色子尚未被发现时(当时格拉肖教授正提出没有Z玻色子的解决方法),统一基本粒子的电磁作用与弱作用的基本模型还只是理论层面的想法。其时,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兴建了质子-反质子粒子对撞机以搜索W及Z玻色子,最终在1983年取得被发现的重大成果(并藉此获得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顶夸克和希格斯玻色子相继在1990年代及2012年被发现,同时我们对中微子的认识也日益加深,这使我们能完全证实电磁作用与弱作用的统一。再加上量子色动力学(QCD)在强力(核力)研究上的发展,今日我们可以宣称已经完全了解所有可见的力及物质,而我们将其称之为标准模型。当中大部分发现都是来自于费米国立加速器实验室或欧洲核子中心的粒子对撞机。
自1984年,世界上芸芸精英深入地研究弦论。标准模型的成功让我们走得更远,将宇宙学推向另一个高峰。同时,高能物理学界亦在急速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国际社群。整个高能物理学界的中心亦已从美国转移至欧洲,许多国家派出队伍参与欧洲核子中心大型对撞机相关实验。同时,亚洲研究组织的重要性也日渐提高。未来20年高能物理的发展仍充满未知之数,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新时代粒子对撞机将是未来科研发展的必要因素。
假设中国决定建造巨型粒子对撞机,整个高能物理学界的中心将转移至中国;假如欧洲持续围绕巨型粒子对撞机的研究计划,他们依然是21世纪内的研究重心。基于现有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正进行的研究计划,欧洲方面将在未来5至10年皆没有开展新计划的余裕。这个正是中国要挑战成为高能物理研究龙头的黄金机会,如中国能够在这时候建造新世代粒子对撞机并在5至10年后展开相关研究,在高能物理研究社群不能亦不会同时支持两个巨型对撞机的假设下,整个研究重心将彻底转移。
的确,以上的研究成果需要昂贵的巨型对撞机以及庞大的研究团队,这与个人(或小的科研组)为中心的研究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但面对如此巨大的科研难题,这却是无可避免的。与其他科学领域比较,高能物理学者在个人层面的资源投入并不比其他多,然而,我们需要把所有资源集中才能加强研究协同效果。惟巨型对撞机的相关研究会将来自世界各地研究者们的资源和技术紧紧靠拢,预计花上一段以十年计的时日研究下,产生巨大的国际协同合作效果,这正是其他科研项目所没有的特质。如果中国决定建造它,它会立即带给中国国际声望和科学影响力,类似AIIB公布时立即给中国带来国际威望和金融影响力。
当我们都把各自的资源集中,人类文明才有长足发展。如我们都只为自己的家庭谋生,把时间都花在打猎农务上,学术发展就会裹足不前。哲学家和学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家和学者,有赖于其他人能够补足他们日常所需。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的追求变得更加繁复,更大的团队(包括基建、跨学科协作实验、建造国际太空站等)变得日益重要。现在,高能物理学者是基础科学上的大型协作的前驱者,而当需要的时候,其他科学领域,例如基因组学、脑启动计划等等、也向同一个方向迈进(雷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为探测引力波而组成一个千人队伍也是一例)。迄今,许多的科研计划皆是由大量跨种族、宗教、国籍、文化的科学家共同努力,不分你我地向着同一个目标奋斗而成,这正展现人类文明的美好一面。比起日趋强大的武器和军备,科研计划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着更好的效果。
我曾经说到杨教授并不支持别人将他在1954年所提出的想法应用到1970年代去建构电磁、弱力之间和强力的模型。这牵涉一个有关对称的哲学思考。你想象一个人的脸容,这应该是左右对称的模样,没有人喜欢一个不对称的脸容,这代表着一种「左、右对称的失衡」。对称同样在物理学上,甚至杨教授的研究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954年,杨教授和罗拔·米尔斯发表的杨-米尔斯理论就是从一个美丽深入的对称中延展(杨教授的学术论文中所展现的透彻,层次以及远见,实在是科研发展上的瑰宝)。但是,当他的理论被用作统一基本粒子的电磁作用与弱作用时,科学家们使用的是破缺的对称性,这或许是杨教授不喜欢的原因。而在量子色动力学上的核力发现当中,杨-米尔斯理论被完整延伸应用,但背后美妙的色对称却被彻底隐藏。如色对称被隐藏,色对称的美又如何得以显现呢?不论如何,杨教授没有继续依循这个方向研究,而我们粒子物理学专家则从1970年代开始一直依循这个方向努力至今,取得辉煌成绩。
带点讽刺地,如杨教授般深深喜爱对称的科学家,他最突破性的发现在于1956年和李政道教授一同发现的宇称不守恒(左右对称的失衡)。前文中我提到,今日我们可以宣称已经完全了解所有可见的力及物质,那为何我们还需要新的巨型对撞机呢?答案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远不是基础物理的尽头。我们今时今日能够测量的只有全宇宙所有物质当中的5个百分比,其余的全部都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我们都还没有清楚这些物质的本质是什么。对于这些的理解,我们今日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当中,唯有通过科学实验我们才有机会认证这些物质的本质。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以下的几个问题有待解答:
? 质量等级差问题
? 超对称粒子是否存在
? 弦论的特有现象
? 更多的未解疑问
天体物理学或宇宙学的研究或地下实验或许有助于解决以上的疑问,但却没有任何研究能媲美新的巨型对撞机更能准确探测更高的能量标度。随着各方面的协作,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将达到新的层面。
一个新的粒子对撞机对中国来说是否过于昂贵?这需要由中国的领导层去决定。但我们可以想象最坏的情况会像1990年代的超导体超级巨型粒子对撞机(SSC),或者是前几年的激光干涉仪空间天线(LISA)一样,在通过计划几年久后美国政府就决定搁置,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我个人非常同意还有许多其他科研项目也值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我相信兴建巨型粒子对撞机并不会限制其他方面科学的发展。有时候我们容易忽略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在科研发展的投入是不断提升的。翻看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供的全球数据(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 2016,图4-8;最新数字截至2013年,使用更可靠的购买力平价PPP) [2] 显示,中国在过去数十年来,每年投入在科研的资源增长达到近百分之二十。2016年追平美国(达到每年近5千亿美元),甚至超越美国只是迟早的事。这增长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在科研的投入预计能增加一倍以上,达到每年1万亿美元。在针对巨型对撞机政府需要花上大约每年5亿美元的预算下,平均每年巨型对撞机所耗用中国的研发预算其实所占不到0.1个百分比(千分之一)。兴建巨型粒子对撞机不会限制中国其他方面科学的发展。
那中国应该减少科研预算而转移投入到其他社会项目当中,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素吗?许多人会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科研可能是提高民生和社会整体经济的最有效方式。我们可以参考欧洲的同类型数据。在1980年代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准备兴建质子对撞机LHC时,当时的投入对于整个欧洲科研来说可是相当巨大的。但在兴建质子对撞机以后,我们可见其它科研成果也获得了显著提升。由此可见,兴建质子对撞机不单没有对其它科研发展造成限制,相反,粒子对撞机所显生之研究成果加强了欧洲推动科研的信心及持续投入。显而易见,这笔为数不少的投入没有一分钱是枉花的。
戴自海
2016年9月,香港
原文点击:http://t.cn/RVSul3i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