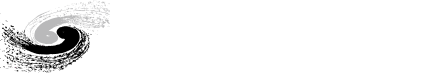走近大科学工程
本报记者 崔 爽
天安门广场向西约15公里,形似一只羽毛球拍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部分结构由北向南卧在地下,它由一台长202米的直线加速器、一组共200米长的束流输运线、一台周长240米的储存环加速器、一座高6米重700吨的大型探测器“北京谱仪”和14个同步辐射实验站等组成。
除了2004年至2008年进行的重大改造工程以及每年的检修时间,在这个地下的庞然大物里,正负电子几乎一刻不停地对撞,产生各种粒子事例,由布设在对撞区周围的谱仪捕捉,再由科学家初选出事例、进行物理分析。
进入中科院高能物理所44年,张闯几乎参与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及其重大改造工程的全过程。“在世界上最权威的粒子数据表上,北京谱仪测量的数据超过1000项,每一项数据就是一项成果。可以说,粲物理领域的绝大多数精确测量都是北京谱仪合作组完成的。”张闯很骄傲,他和他的同行,见证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就的粲物理领域30年领先。
超高能研究必须对撞
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北京谱仪III发言人苑长征介绍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一台高能加速器,它提供的正负电子束流主要做两件事:一是高能物理实验,即北京谱仪实验,产出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二是同步辐射应用研究,也就是利用对撞时产生的同步辐射光供诸多学科领域开展研究,每年有大约500多个实验在这里完成。
张闯研究员展示了一张漫画,两只小松鼠站在机器的两头,手中各拿着一个核桃,“把核桃往地上扔可能打不开,但让两个核桃高速对撞可能就能撞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把粒子对撞打开,看里面是什么东西。速度越快、撞得越碎,越可能有所发现。”他用这个例子解释了“为什么要对撞”。
“如果不对撞,而是用电子束打静止靶,产生的有效的相互作用能量要小得多。1954年,著名的物理学家费米提出建造质心能量为3TeV的高能加速器,按当时的技术,采用打静止靶的方案,需要加速器的半径达到8000公里,比地球还要大;而欧洲强子对撞机的半径只有4.3公里,就达到了13TeV的质心能量,所以超高能研究一定要让两个束流进行对撞。”张闯说,但是束流对撞要求粒子多、截面积小、频率高,才能获得足够高的对撞亮度,因此难度也大得多。
“正负电子不断对撞,科学家获取分析对撞产生的大量事例,看其中是否可能有一些稀有现象,披沙拣金一般,各种新粒子都是这样现身的。”张闯说。
在亿万粒子中找不同
在粲物理领域,绝大多数精确测量都是北京谱仪合作组完成的。
这来源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卓越性能。“1988年10月16日对撞成功,运行30多年。对撞机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做出来的,我们这一代曾面临康奈尔大学的挑战,对方把能量降下来和我们竞争,一时间超过了我们,我们做了重大改造,在世界同类型装置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张闯说。2004年改造以前,对撞机以一对束团,每秒对撞约一百万次,2008年完成改造后,它成为目前的双环结构,约100个束团,每秒对撞约一亿次,加上其他性能的提升,亮度比改造前提高了100倍。
在粒子物理领域存在三个研究前沿,分别是高能量前沿、高强度前沿、宇宙学前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处于高强度前沿,另外两端分别有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国际直线对撞机(ILC)、未来环形对撞机(CEPC和FCC)等和高山宇宙线、空间探测器、望远镜等。
站在极广大和极幽微的端点,物质结构研究尺度不同。张闯的讲述中,在20世纪初,人类认识的世界小到10的-10次方米的原子,大到10的11次方米远的行星。到1930年代,这个范围扩大到原子核和恒星。到了2000年,依托大科学装置,人类的视野深入到10的-18次方米的夸克、扩展到10的25次方米远的浩瀚太空。对物质结构的探索是人类一步步走出洞穴的过程。
令人惊喜的是,接受采访时,苑长征表示最近有一个重要发现:北京谱仪Ⅲ合作组(BESⅢ合作组)发现正负电子对撞中兰布达超子存在横向极化,合作组利用2009年和2012年采集的13亿粲偶素数据,选出了纯度高、质量好的42万事例,发现由此产生的兰布达超子存在高达25%的横向极化。这项成果刚在英国《自然·物理》杂志刊出。
为牵头大科学计划树立规范
张闯打开电脑,进入对撞机的显示页面,屏幕上两条曲线沿时间轴向前推移,一条代表正电子流强的红线,一条代表负电子流强的蓝线,高点约在600毫安,大概一小时后,两条线匀速降至低点,约450毫安,这代表粒子数量越来越少,控制室的工作人员操作按键,注入正负电子,曲线抬头,继续每秒一亿次的对撞。
来自全世界14个国家、64所研究机构的400多名科学家,每天都可以在世界各地点开这个页面,看到两条曲线。
“从1989年开始实验起,就建立起北京谱仪合作组,这个合作组三十年来一直在一起做实验,是很不容易的。”张闯说,这套由中国牵头的国际重大科学装置的合作规则,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宝贵经验,为后来者做出示范。
它将来会不会寿终正寝?张闯很坦然:我们的优势还会保持十年以上,这十年要继续做实验,比如继续研究轻强子谱和新强子态等,根据实验结果,看是否需要进一步提高性能。
近几年,关于中国是否要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争论持续进行。去年底,两卷本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概念设计报告》正式发布。前几天杨振宁在公开演讲中重申反对建设的观点,再次将争论摆上台面。
“有争论很正常。”张闯不假思索,“但科学研究会找到自己的方向,比如我们的对撞机继续向前走,有需要可能再改造。如果暂时不能做高能量前沿,还可以做高强度前沿。如果因为经费或者技术原因不能做,可以等将来成熟了再做。”
“但最好能尽快挺进高能量前沿。”他补充。较量不可避免,“除了欧洲的FCC,日本还可能要做ILC,国际上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当然,希望下一代最强对撞机依然在中国。”张闯笑说。
来源:《科技日报》2019年05月22日头版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