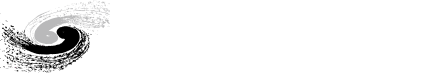2012年3月8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代表大亚湾中微子研究团队宣布,发现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被称为“中微子研究道路上的里程碑”。然而王贻芳和他的团队显然并不止步于此:正在建设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基地将自主研制更大的探测器并预计于2020年建成开始运行,届时中微子的质量顺序有望在实验中测出,成为中微子研究的下一个重大突破。
实际上,几十年来包括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都在试图寻找中微子并弄清它精灵古怪的“脾气”。科学家相信,中微子的深入研究将揭示宇宙演化的重大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只大部分是物质而不是反物质等。
这并不容易。虽然时时刻刻都有中微子像无数的流星一样划过天际,穿越我们的地球和身体,但它们非常轻,而且调皮,难以抓住。中微子还有三种“味道”,即电子中微子νe,缪中微子νμ,陶中微子ντ,要搞清楚“三种味道如何混合”,每种中微子的绝对质量多少,以及更多的相关问题,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在王贻芳看来,中微子研究虽然难度大,但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不管是团队还是技术在某些方面都有冲刺世界第一的实力。不过他进一步表示,虽然中国在中微子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大科学研究包括高能物理研究还存在前瞻性不够、轻重不协调、资助体制不合理等问题,尚需要建立更好的顶层规划及完善支持大科学研究的体制机制。
中微子研究的下一步
NSR:众所周知,中微子研究是高能物理和天体物理都很关注的热门领域,历史上也4次获颁诺贝尔奖,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原因?
王贻芳:从泡利1930年提出存在中微子的假说,迄今有近86年。从首次探测到中微子算起,也有60年历史。中微子之所以很热门,是因为它涉及的问题极为根本,牵涉人类对宇宙的根本认识,中微子影响着宇宙的形成与演化。比如说,中微子振荡的电荷-宇称不对称性很可能是宇宙中物质-反物质不对称性的起源;而且由于中微子几乎不与物质相互作用,穿透能力强,是独一无二的研究天体内部的探针。
NSR:中国在中微子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实验方案和目标选择上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呢?距离大亚湾实验宣布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已经4年了,江门实验也在筹建,下一步的实验目标是什么?
王贻芳:一般来说,研究中微子的路径大概有利用太阳中微子、大气中微子、反应堆中微子、或加速器中微子等四种。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实际是利用核反应堆来探测中微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太阳中微子和大气中微子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精彩的工作,确定了中微子振荡六个参数中的三个半,其中太阳中微子振荡确定了sin22θ12~0.86和Δm221~ 7.5x10-5eV2,大气中微子振荡确定了sin22θ23~1和|Δm232|~ 2.5x10-3eV2(没有确定其符号,算半个参数),剩下的两个半参数包括混合角θ13、|Δm232|的符号(中微子的质量顺序)以及CP破坏相角δ,我们预计θ13可以在反应堆产生的中微子振荡中被精确测出来,因而向这个方向努力;二是大亚湾核电站的天然优势,不仅核反应堆功率大,而且核电站周围有山屏蔽,为去除本底提供了便利。
大亚湾实验从2007年动工,2011年逐步完成探测器的安装,随后在短短的55天测出sin22θ13为9.2%,超出了预期,而且sin22θ13>0.01表明用现有技术就可以测量质量顺序和CP破坏。
因此,很自然我们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江门实验中解决中微子质量顺序的问题。正在我国广东省江门市建造的江门(JUNO)实验将利用两万吨的液闪探测器在距核反应堆53千米处精确测量反应堆中微子的能谱,从而推断出中微子的质量顺序。
NSR:这算是半个参数?
王贻芳:对,确定到底是m3>m2还是m3<m2,另外我们希望到2030年左右把江门实验改造为能验证中微子是否为其自身反粒子的实验,主要是通过寻找无中微子的双贝塔衰变反应。这个实验花钱也不是很多,但具有国际竞争力。
NSR:那中微子振荡的另一个参数CP破坏相角δ江门实验会测量吗?
王贻芳:不会。CP破坏相角目前是日本和美国在测量,这样的实验同时需要中微子和反中微子两种源,只有加速器才能实现,但建造加速器非常昂贵,我们目前没有什么优势,暂时不做。
NSR:除了上述提到的中微子振荡参数问题,中微子研究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挑战?
王贻芳:还有好几个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是多少?惰性中微子是否存在?中微子究竟是狄拉克粒子还是马约拉纳粒子?还可以利用中微子作为探针去研究宇宙起源和演化过程等等。
高能物理的研究方向选择
NSR:实际上,除了中微子,高能物理也有很多热门的方向,中国该如何选择?是应该分散资助不同的项目还是集中力量来突破优势方向?
王贻芳:在高能物理领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课题,但最后选择什么样的课题来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我个人认为,选择方向跟资助资金、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有密切关系,如果我们有优势我们可以自己来牵头、主导,比如大亚湾项目,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加入国际的大科学研究计划。
NSR:我们自己牵头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
王贻芳:“牵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项目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由我们担任,另一个含义是指在实际工作中,项目的想法和设计由我们提出,我们能够掌控项目进程,掌握核心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中国境内的大科学项目都是由我们的科学家来牵头和主导的,本世纪的大亚湾实验和筹建的江门实验也由高能所来主导。
NSR:这些项目的国际参与度如何?
王贻芳:一般来说,大科学计划尤其是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项目都是多国合作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实验以及江门实验都有国际参与。北京电子对撞机一开始是美国帮助建设的,建成以后美国就关闭了自己国内的加速器,因为我们对撞机的指标已经达到当时世界的最好水平,美国的科学家就到中国来参加我们的实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于2002年再次升级,2008年重新投入运行,到目前为止已经运行超过30年。
也正是这30年的积累,使得我们有能力来牵头并主导大亚湾实验和后续的江门实验。大亚湾实验美国出资30%,江门实验由于他们有自己的中微子实验所以没有继续投入,改由欧洲出资。整体来看,江门实验的国际出资比例大概达到了20%。
NSR:在出资比例上,国际有什么惯例吗?
王贻芳:很难说有统一的惯例。比如大型强子对撞机,欧洲出资80%,美国和日本一共出资20%,项目主要由欧洲来主导,被认为是合作成功的典范。相比之下,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有35个国家参与,却一直磕磕绊绊。ITER项目欧洲出资45%,包括美、日、韩、俄罗斯及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出资55%,由于出资比例均衡,没有形成优势明显的项目牵头和主导方,导致项目陷入反复的会议商讨中,天天忙于投票,却不能有效推动进程,应该说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所以说一个项目的主导国家应该承担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出资比例一般应该超过50%。我个人认为,80%,20%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出资比例,70%和30%也可以,低于这个比例就比较难了。
NSR:中微子研究是中国主导的一个成功案例,但毕竟是少数。最近引力波的重大发现也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引力波的项目也纷纷露出水面,您怎么看?
王贻芳:老实说,这次引力波的探测项目中国的参与度比较低,没有进入核心的设计和技术研发,只有清华大学的两个学者参与了数据处理。
至于为什么中国的引力波项目在国外取得重大突破后才“纷纷抬头”,我认为是国内对于像引力波探测这样的大科学计划还是没有整体的布局和顶层规划,同时对自身研究队伍的优势和劣势没有充分认识,而且对研究失败容忍度不够高,导致我们的“跟风”式科研。高能物理的研究布局通常都要规划10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于引力波而言,中国到底要不要做,是参与国外项目,还是要自己做;自己做是做地面探测还是做空中探测,以及我们有什么样的技术积累和团队等问题都需要厘清。
NSR:除了中微子外,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研究也很热,国内布局如何,也有这样的问题吗?
王贻芳:国内有很多人在做暗物质研究,相似的项目投了好几个,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合力,暗能量研究国内的投入很少。
我们认为暗物质确实是存在的,但如何去寻找还有待商榷。我们知道自然界一共有四种作用力:引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以及弱相互作用。提出暗物质的存在是因为它的引力效应,但无法通过引力直接探测,要通过假设它参加弱相互作用来探测。实际上,现在的实验设计如果没有这个假设,以及其密度和数量是可以探测到,实验就没有办法进行。
世界范围内科学家为了寻找暗物质不断提高探测器的灵敏度,过去的十几年间探测器灵敏度已经提高了10个量级,但仍然没有找到暗物质的确切证据,如果灵敏度再提高下去,那可能就会达到中微子背景的极限,也就是说看到的都是中微子形成的背景信号,而非要寻找的暗物质了。
NSR:丁肇中的暗物质探测器AMS风险是否会小一些?
王贻芳:丁肇中的实验也是基于暗物质的弱相互作用,通过观测正、反暗物质粒子湮灭产生的γ光子及正电子来验证暗物质存在。到目前为止许多实验已经把低能区排除掉了,需要不断往高能区搜索,但高能区暗物质的密度会低得多。
NSR:丁肇中的实验曾经说发现了一些暗物质的迹象。
王贻芳:对,AMS在410亿个初级宇宙射线中,共观测到约1000万个电子与正电子,这是迄今为止最精确的太空电子和正电子能谱测量,而正电子能谱是识别暗物质的重要指标。丁肇中曾表示,AMS已确认暗物质5个特征中的4个,还有最后一个特征有待确认。
NSR:最后一个特征是什么?
王贻芳:是看正电子能谱在高能端是否会有一个骤降,如果有,说明它是暗物质粒子湮灭产生的。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当然,丁肇中对同行是这样解释AMS实验的:我们有可见光、红外、射电等各种各样的望远镜,但我们很少有探测带电粒子的望远镜,AMS是世界上第一个高精度的,值得发射到天上看看结果如何。这个立场和研究理念当然是站得住脚的,AMS如果能够找到暗物质最好,没有找到也有它自身重要的科学意义。
发展高能物理的必要性
NSR:很多人认为高能物理是阳春白雪,花费巨大,而且风险也很高,不如将经费投在小科学、小团队上,您怎么看?
王贻芳:其实中国高能物理项目的支持政策并不完善,而且力度也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尤其是年人均经费并不比其他领域高。如果问我中国到底要不要发展高能物理,要不要大科学研究计划,我的回答是一定要,高能物理研究不仅是科学探索,为全世界的科学发展做贡献,也会带动本国产业的核心技术进步,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升级的时候需要用到超导设备,但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当时也考虑过是否从国外买,做了招标。竞标的时候,日本公司给我们的价格是6000万元人民币,加上附加设备可能要到7000-8000万元人民币,但我们的预算根本没有这么多,怎么办?最后被“逼上梁山”,自己去设计、制造,2000万成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超导设备的自主研制,成功将研究所的技术转化到工业界,还带动了民用核磁共振设备的研发和生产。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升级的时候产生的。当时我们需要在一个(直径)2米的圆盘上面打3万个孔,每个孔的精度20 μm。在跟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成飞”)合作的过程中,高能所的研究人员在成飞和对方的技术人员同吃同住6个月,从原理开始摸索,一点一点找问题,终于把精度从成飞最初的精度从200 μm提高到了20 μm,大大提高了成飞的工艺水平。
正在筹建中的江门实验,需要的最核心部件包括液体闪烁体、光电倍增管等,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世界最好。比如我们将要做一个直径35米的有机玻璃球和透明度在25米以上的液体闪烁体,全部依靠自主研制,而且性能要超过国外。
NSR:换句话来说,高能物理的研究可以带动国家的工业发展。
王贻芳:是这个意思。有很多人说高能物理是濒临死亡的科学,我觉得不准确,至少在我们国家现阶段,高能物理的发展是必须而且必要的。
我们回头来看美国的科学发展历程。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美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这些人很多成为仪器公司的创业者及关键技术人才,我们用到的很多进口物理、化学、生物仪器就是这些人研发出来的。
我们现在大科学工程的投入大概在2-3亿,牵扯到的工业企业有数十个,假如投入100亿那就能带动几百个企业,那我们工业研发和制造的水平就起来了,也能够自主研发化学、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仪器了。
大科学合作
NSR:合作是科研中永恒的话题,对于像高能物理这样的大科学计划来说,合作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王贻芳:我觉得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应该是全方位、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
首先,从顶层规划开始,资金资助部门之间需要合作。科技部、自然基金委、财政部应该协商制定针对大科学计划的资助政策。中国在高能物理项目资助体制上的短板现象很突出,比如没有比较专业的评审专家,没有统一的部门来负责项目的资金支持、制定长期的研究计划,导致一些有潜力的项目被拖延甚至被砍掉。
在具体项目上,项目评审可以请国外专家参与,这种参与不仅要评价项目本身的研究意义和可行性,更重要的是要有国际资金投入,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大亚湾实验和江门实验,美国和欧洲分别都投入了30%和20%的资金,只有真金白银的投入才算对项目的真正认可。反观国内,高能物理项目的经费申请没有特定的归口,科技部、基金委基本是以资助小科学研究的模式来设定各种基金,而且这些钱往往又分到各个小课题组,文章和专利是主要的评价指标,没有大项目、大合作的概念。因此,国内的很多大科学研究计划,有和地方政府合作要钱的,有从学校找钱的,纷纷各显神通,项目申请非常耗时、耗力。
NSR:项目资助需要多方合作,在项目立项以后需要合作的地方更多。
王贻芳:是这样。一个大的科学计划有几百人组成是很平常的事情,团队成员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如何合作对于顺利推进项目非常关键。
NSR:中国的科学家尤其是年轻人在和国外团队成员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障碍?
王贻芳:我认为主要是语言和文化的障碍。通常来说,项目讨论的语言是英语,大家有不同意见就要争论。英语母语的人很容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一般很难用西方人理解的方式去争论,对于通过友好辩论来解决问题的技能训练不足。我们国内现在整个的体系都是这样,比如现在开个会论证一个问题,没有意见才好,一有意见这个事情就不知道怎么办。
NSR:大亚湾实验也涉及国际合作,你们是怎样鼓励国内的学生克服交流障碍的?
王贻芳:很幸运在大亚湾实验启动时,我们吸引了一批国内最优秀的学生。与国际团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逼着年轻人在讨论时,有不同意见要敢于发表,要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鼓励他们积极在国际会议上做演讲,跟同行交流。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很有效,大亚湾实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高能物理人才,他们已经在业界内崭露头角,很多学生即将毕业时就收到了国外知名实验室伸出的橄榄枝。不过因为他们觉得大亚湾实验已经是世界上同类研究最领先的,希望能够继续在最顶尖的研究环境中工作,所以选择留下来。
NSR:除了国际合作,像大亚湾这样的大科学计划跟国内的合作也非常多。你们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吗?很多国内所谓的“大项目”最后出现立项时大家凑到一起,分完钱又各做各的情况。
王贻芳:高能物理自身具有大科学研究特点,国际上高能物理的项目脱胎于军事研究,一直都有大合作、大研究的传统。像大亚湾项目,主导单位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大部分人员也来自该所,有利于高效的合作。
NSR:现在的评价体系也都是以小科学的评价为主导,强调独立贡献,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你们怎么解决年轻人的评价晋升问题?
王贻芳: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在大科学项目中,大家分工协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贡献,但确实不好通过发表论文的署名次序来评价每个人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但通常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团队内部每一个人做了什么,做的怎么样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在国际上也能得到认可。就我们自己的情况来说,高能所内部的年轻人,只要在项目中确实做得好,通过同行评议就能得到晋升。但外部的一些奖励比如说“杰出青年基金”等我们比较少,因为难以满足所谓的“独立贡献”等评价指标。
NSR:脑科学研究也是大科学研究计划,也需要几百人的团队,但是团队组织很不容易。
王贻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科研资助体系和评价体系建立在小科学概念的基础上,没有充分考虑大科学的整体性和合作性特点。随着科学的发展,生物学领域研究逐渐也朝着交叉和大型化发展,像人类基因组计划、干细胞、再生生物学、脑科学计划等都是大科学项目,遗憾的是我们的资助和评价体系还没有完全赶上这个趋势,导致科学家之间合作的积极性不高。
NSR:现在国家也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你认为是否能解决合作难的问题?
王贻芳:我不敢肯定。大科学计划意味着大的投入到一个团队,没有人能保证项目一定能成功,因此资助方也会因此而担风险:为什么要投一个可能失败的大项目,让没有分到钱的人不满意?还不如把钱分散了,大家都拿点小钱,皆大欢喜。如果没有勇于担责的机制以及容许失败的氛围,大团队合作的大科学计划并不会更容易。
未来可期
NSR:高能物理未来还有哪些有趣的挑战?在更高能部分是否需要更大的理论体系?
王贻芳:世界范围内的高能物理研究都还在继续建造新的高能加速器,以期发现新的粒子和新的模型。对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来说,它预言的东西基本都已经被验证了。中微子性质的一些新发现可能会突破标准模型。进一步来说,标准模型并没有对更高能区域加以预言,是一个低能有效的理论,并非终极理论。目前的实验结果已经可以看到将标准模型简单外推到高能领域是不合适的。
NSR:还会需要新的理论吗?
王贻芳:为了解决高能区域的问题,物理学家想出了五花八门的理论,其中两类比较受欢迎:一类是超对称,另一类是多维空间。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现有的理论可能都不对,因为并没有实验结果验证。
NSR:所以建立新的高能加速器很重要。
王贻芳:对,新的高能加速器能帮助我们发现标准模型之外的新物理疆域。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将继续运行到2030年代,并且正在考虑未来环型对撞机 (Future Circular Collider, FCC)的可能性;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筹划国际直线对撞机(International Linear Collider, ILC)的建设。我们最近也提出了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ircular Electron-Positron Collider, CEPC)计划,并在随后可以有一个超级质子-质子对撞机(Super Proton-Proton Collider, SPPC)。因为中国应该也有能力去主导这样大型的高能物理研究项目。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计划是基于过去30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和国际合作经验的基础上的,并不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
NSR:对于任何科学研究来讲,最重要的还是年轻人的培养,高能物理学界在国内能够吸引足够多的优秀学生吗?
王贻芳:我觉得关键在于我们做的研究是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如果是,年轻人能够看得到,也会愿意留下来。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中培养的年轻人有大约90%都留下来了,就是因为我们处于领先的地位。
英文原文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 第3卷第2期,原标题为“Yifang Wang: high energy physics in China”。
附件下载: